编/者/按
江苏作协“名师带徒”计划源于2018年10月省委、省政府《实施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工作方案》,共有20对文学名家与青年作家结为师徒。厚培沃土,春播秋收。在此,我们开设“‘名师带徒’计划成果展示”栏目,展现文学苏军薪火相传的良好态势。
一、张羊羊简介

徒弟:张羊羊
张羊羊,1979年5月生于江苏武进,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钟山》《十月》《大家》《星星》《扬子江诗刊》《中国作家》《天涯》《散文》《山花》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多篇。出版诗集《马兰谣》《绿手帕》、散文集《草木来信》《旧雨》《庭院》等。曾获江苏省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2014年江苏优秀科普作品图书类奖。
二、张羊羊创作成果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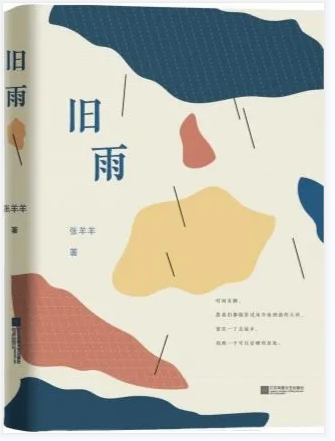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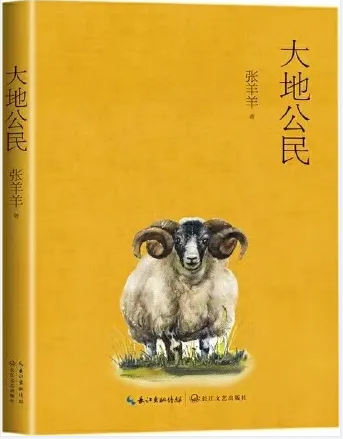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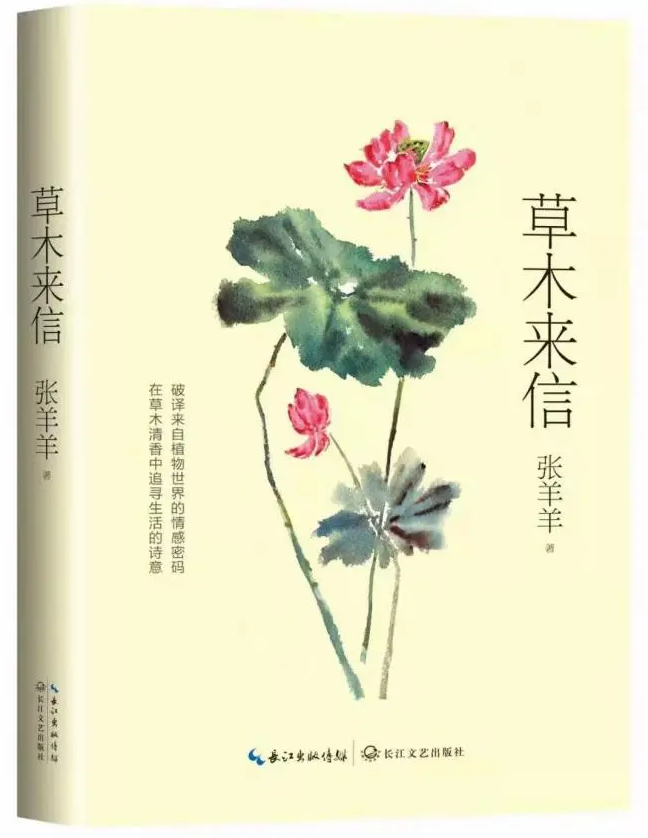
2019年
发表
散文《旧雨》,发表于 《散文》2019年第5期
组诗《不惑之年》,发表于《飞天》2019年第5期
组诗《平原故事》,发表于《扬子江》诗刊2019年第4期
散文《大地公民》,发表于《大家》2019年第5期
散文《脸》,发表于《天涯》2019年第5期
散文《草木来信》,发表于《西部》2019年第5期
组诗《时间纪》,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2019年第10期
散文《大地公民》,发表于《散文海外版》2019年第12期
散文《旧雨》,发表于《香港文学》2019年第12期
2020年
发表
组诗《月亮向西》,发表于《星星》2020年第1期头条
组诗《谜语》,发表于《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1期
散文《草木来信》,发表于《朔方》2020年第5期
散文《大地公民》,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2020年第7期
转载
散文《大地公民》被《散文选刊》2020年第3期转载
2021年
出版
散文集《草木来信》,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散文集《旧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散文集《大地公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发表
散文《锅碗瓢盆》,发表于《西部》2021年第2期
组诗《平原故事》,发表于《中国作家》2021年第3期
组诗《太阳落山》,发表于《飞天》2021年第3期
散文《草木来信》,发表于《黄河文学》2021年第3期
散文《脸》,发表于《雨花》2021年第8期
散文《故乡的食物》,发表于《香港文学》2021年第9期
三、张羊羊作品节选
《燕笋》
竹子长大了可以做鱼竿,编篱笆,妈妈们还用来晒衣裳。竹子小的时候,叫笋芽儿,很嫩,很好吃。那一抹淡紫透了出来,缀了细小露水,泥土仿佛有了眼睛。
“燕笋出时斑豹美,凤花开处杜鹃啼。”我没见过斑豹,那当是很美的样子,反过来想,它就穿着燕笋那样的衣裳。
韭菜也慢慢葱郁。
韭菜与笋,都抖落着土粒,却无丝毫浊气。
那么好的笋,那么好的韭菜,炒在一起,给了我一段过去了很久的忧伤的好时光。八岁的孩子快有一米二的个头,他在写第一篇作文《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喜欢做饭,他做的菜色、香、味俱全。
我读了,有点儿捉襟见肘,刀板上没有几支十几二十厘米长的燕笋,还谈什么做拿手好菜呢?
冬笋吃了很长一季,有时炒雪菜,有时炖排骨,有时煨老母鸡。燕子回来了,也到了吃燕笋的时节,可我四处找不到一片小竹林。
平原上的燕笋秀气,长着南方水乡的小性子,剥完笋壳后肌肤细腻,嫩绿嫩绿的。不像那些毛笋、山笋,切片后得用水焯一下,才能去涩味。小燕笋还没入口,看几眼,就有“秀色可餐”的美妙。
我和那个宁愿没有肉吃也不能居所无几枝竹的人不同,我可以不吃肉,有没有竹子在屋旁无所谓,那几棵燕笋的小身体,好是馋人。像奶奶做的“月亮饼”,总给我几分念想。
人有念想,好像能多留住一丁点故乡。张季鹰想的是莼菜和鲈鱼,黄景仁想的是燕笋和刀鱼,都是一道素菜一道荤菜,但俗气点比一比,黄景仁的念想要比张季鹰的名贵一点,刀鱼的口感也不是鲈鱼可以相提并论的。黄景仁与我同乡,我也更能觉知他那“江乡风味,渐燕笋登盘,刀鱼上筋,忆著已心醉”的情感。
燕笋季节,除了刀鱼,还有一种被食客们反复念及、咂嘴的鱼,它叫河豚。所以我们那有一道菜,名为“燕笋河豚”。如果这道菜里,用毛笋替代燕笋,怕是要糟蹋了河豚。当然,我对河豚没什么兴趣,河豚汤汁里的金花菜味道极佳,若换上燕笋,则更是妙不可言了。
黄景仁送别万黍维归宜兴时,曾赋诗“语我家山味可夸,燕来新笋雨前茶”,又提到了燕笋。和笋并列的,则也是我一生爱好的东西。有时想想我也挺感动的,出生的地方,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关照着我们的口舌。
有年我在浙江长兴喝到一种茶,那鲜茶芽叶微紫,嫩叶背卷似笋壳,所以取名“紫笋茶”。初听,像是把我的两种心爱之物合并到了一起,一口春天下去,幸福得简直有点眩晕。
但紫笋茶是茶,没有笋的味道。
写燕笋不想写长,春天眨眼过去了一半,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吃到燕笋。
其实,我对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最初阅读是那本《金蔷薇》,但与其说记住了他的名字还不如说记住了他笔下那只因为试图偷吃他煎锅上的土豆而烫伤了鼻子的小獾子。那个事件里,他身边有个善于虚构的九岁的孩子,而大人们却极喜欢他的种种虚构,比如孩子一会说听见了鱼儿喁喁私语,一会又说看见了蚂蚁拿松鼠皮和蜘蛛网做成摆渡船用来过小溪。确实,换作我,我也喜欢这种虚构,也舍不得捅穿这种美妙而温情的虚构。无论在哪里,孩子们总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美好事物。
那个孩子在獾子烫伤了鼻子的第二天早晨叫醒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看见獾子在医治烫伤的鼻子,孩子拉起他的手要去证实自己没有撒谎。随即,在他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獾子在一个树桩中心挖了个窟窿,把烫伤的鼻子埋进那儿潮湿冰凉的烂木屑以使得鼻子凉快一点。他还看见,那只獾子坐下哭了起来,圆圆的泪眼,一边呻吟一边用粗糙的舌头舔受伤的鼻子……我忍不住也揉了揉鼻子,仿佛某年某月某日的傍晚,我饥肠辘辘放学归来看见母亲做好的菜肴,探鼻一闻不小心被热气烫着了一般。那一刻,我像极了那只小獾子。
以上,是我对獾子的间接认识。在没有山丘、森林的地方,我那些没有被烫伤鼻子的美食家朋友总能嗅到特殊的味道。时常穿过两三条巷子,在某个不起眼的小餐馆坐下,作为老主顾的他们,想吃什么老板心领神会,然后从冷藏柜里掀开第一层的肉类块状物,掏出下层大大小小、一坨坨的肉类块状物。稍会工夫,几个热气腾腾的锅仔摆在我们眼前,在经过老抽装饰一番后,会有人教我辨识什么是麂子、什么是野猪、什么又是獾子。这里,才是我直接认识獾子的地方。而我实在是太差劲了,根本尝不出什么是麂子的味道、什么是野猪的味道,什么又是獾子的味道。
我喜欢看它们的样子,看它们在大地上行走,如果能撞见一只獾子来偷吃我煎的土豆也比我能吃到它的肉的欲望来得强烈。獾子有很多种,常见的有狗獾、猪獾和狼獾。这样的区别显而易见,模样长得偏像于另一个物种而已。我所能确定的是,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遇到的肯定不是生活在北极边缘的狼獾。狼獾比较凶残,像狼一样有自己的领地,不太会爱上土豆并且有一双圆圆的泪眼。至于是狗獾还是猪獾,他也没说明白,我从他的描述中更倾向于写的是猪獾。
有时候,我特别想穿上獾子的皮毛,出现在地方志分明记录了有獾子的乡野,因为闻得到伙伴的气息,那些原本以为消失了的獾子们从角落里探出头来。我原来是认得它们的,那个叫小明,那个叫小朋,那个叫小友……我和它们在一起特别快乐,我不再双脚直立行走,那是多么难看的走路姿势啊。我四肢踏地,在草丛中奔跑。头顶有那么多星星,我们商量着今晚的活动,先偷张羊羊家的玉米吃,再把张羊羊那个喜欢吃我们同伴的朋友家的红薯地翻一个遍……等妈妈叫我们了,我们就唱着胜利的歌儿回家去。
“一年以后。我又在这个湖的岸上,遇到鼻子留伤疤的獾子……我朝它挥挥手,但它气恨恨地对我嗤了一下鼻子,藏到越橘丛中去了”,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描述的那只獾子就像一个可爱的孩子,于是我也记住了那只獾子,我还给这獾子取了个名字: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平原上几乎看不见猎人的影子了,平原上的猎人原本就很少,在以耕作为主的土地上,渔与猎属于少数的行为。我想,如果我出生在山林里,摘不到野果,采不到蘑菇,也没有种子,我会不会是一个猎人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大概在皑皑白雪里追踪着脚印,满脑子想着妻儿丰盛的晚餐。而我出生在太湖平原,那里田野肥沃,粮食富足,我和猎人这样的身份产生不了必然的联系。
从前,我并不觉得“猎”有多么的粗暴。一个人和一条狗,因为谋生温情地聚拢在一起,他们在乡间行走,兼含着两个物种间的依附与信任。那时候,我盼望着每天能碰到猎人,看着他举枪、瞄准,“砰”的一声,默契的猎狗也“噌”的一声射向抛物线,将猎物衔回。
那狗衔回一只野鸡或一只野兔,有时候只是天空坠落下来的一只个子不大的鸟。猎人取下猎物塞进挂篓时,不忘轻拍两下猎狗的脑袋。狗总是欢喜地摇几下尾巴,继续跟着猎人在乡间转悠。我觉得我那时和狗很像,那猎人就像乡村小学的语文老师。我也常央求猎人让我看看他挂篓里装了多少东西,他会微笑着轻拍两下我的头,将挂篓摘下,翻转过来倒地上满足我的好奇,然后重新装进去。猎人也一般允许我跟着他一段路,看看接下来的收获。乡间的麦浪里怎么会藏着那么多美丽的小动物呢?没有猎人我总是看不见,好像是猎人来之前刚刚搬进来的。
于是,我成了梦想有把猎枪的孩子,因为再和善的猎人也从来不允许我摸他那把枪。阿克萨科夫在《渔猎笔记》写过,“有些农家子弟每遇猫狗,不是用脚踢,就是用石头棍棒揍,从不轻易放过它们;而另一些农家子弟则相反,他们常常保护可怜的动物免遭自己的同伴虐待:他们抚摩着小动物,与它分享自己并不丰盛的食物。这后一类的孩子一定会成为某种猎事的猎人。”他的对比性描述和肯定语气让我有些疑惑,我正是他所描述的后一类孩子,不仅从未摸过猎枪,长大后更对猎人满怀敌意。可我也很奇怪曾经的小小心灵,为何看着一个猎人打猎的情景会比猎人更忘情呢?
猎人是从远方来的。平原上没有大型动物,所以猎人的挂篓不大,猎物也大多数到附近的集市上卖掉,换取渔民和农民的收成,和平原上的劳作气息相似。猎人不是狩猎者,狩猎好像遛鸟一下,有悠闲气和贵族气。比如非洲日益兴起的狩猎场,可以花钱去买猎杀犀牛、大水牛、羚羊、河马、长颈鹿、斑马、鸵鸟等动物的乐趣和它们的遗体。
也许食肉动物都有占有领地的天性,从我最远古的祖先始,不得不与流血有关。我的祖先曾经是那么地勇敢,在猎杀和被猎杀间,他们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一口气接一口气地生下我们,直到我们变成主宰者。在强大的本能、信念背后,我看见了《吴越春秋》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的娱乐情趣和一代又一代人心灵的衰弱。
我时常会梦见那些猎人,他们机警又舒缓的脚步和猎狗奔跑的速度。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速度呢?“我想起,在乡下/猎人和一只鸟的对峙/那只鸟死了/那个猎人也死了/这期间也就/间隔二十年”。于是我给见过的猎人虚构了一次复活,在二十年后的暮色中,他和他的狗仿佛生了鼻炎,嗅不到一丝猎物的气息。在没有乡野的土地上,他一无所获;他一无所获,我不知道该感到快乐还是难过。
偶然读到清人刘琬怀的《望江南•其二十九杂咏》,“江南好,风味不寻常。席上春盘青笋嫩,茶边寒具玉兰香。那免一思量。”江南不寻常的风味太多了,这画面还真是有点简朴。不过,合我口味。对青笋(莴苣)之爱自不必说了,两道点心也是我非常爱吃的:春盘(春卷)和寒具(馓子)——据诸多考证,恰切地说春卷属于春盘的一种,馓子属于寒具的一种。
转而一想,点心如此熟悉,和刘琬怀似是乡邻。一查,果然,阳湖人。资料甚少,又是一个生卒年不详的女子,嫁给了金坛一个叫虞朗峰的人。母亲是虞友兰,有意思的是她有个哥哥叫刘嗣绾,字简之,和我孩子的名字一样。刘琬怀有《补栏词》,已买不到,从旧书网看到影印本,上面有段跋文:“昔年家园中有红药数丛,台榭参差,阑干曲折,与诸昆仲及同堂姊妹常聚集其间,分题吟咏,填有长短调六十阕,名《红药栏词》。后置之架上,忽尔遗失,未知何人将覆瓿耶。每思及,甚懊恼,仅记得数十首,馀竟茫然。今来京邸,闲窗独坐,怅触无聊,将所记录出,又成数十阕,为之补栏,续成前梦,亦不计其工拙,聊自一叹耳。琬怀记。”
此为题外话。只是读到此段,我能隐约看见一个惆怅的女子在吃着春卷和馓子。
馋馓子了。买回一盒“金丝馓子”,比小时候吃的细而密。大手掰这种小馓子,与以前小手掰大馓子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馓子产地徐州,蝴蝶外形,脆的确脆,至于“脆如凌雪”的味感我倒是没有。《齐民要术》记有细环饼、截饼:环饼一名“寒具”,截饼一名“蝎子”。皆须以蜜调水溲面。若无蜜,煮枣取汁,牛羊脂膏亦得;用牛羊乳亦好,令饼美脆。而那种截饼纯用乳溲者,就有“入口即碎,脆如凌雪”之感。我有点搞不清倒底环饼是馓子还是截饼是馓子了。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写过杭州“夏月卖义粥、馓子、豆子粥”的早市和“冬闲,担架子卖茶,馓子慈茶始过”的夜市,他老是关注馓子,兴许也是一个喜欢吃馓子的人。他还多次提到一种看盘,列了“环饼、油饼、枣塔”,很明显,环饼和馓子肯定不是同一种食物,看它们的叫法,形状就有很大的区别,可能都属于“寒具”。
幸好的是,“金丝馓子”的配料写得明明白白:小麦粉、水、食用盐、大豆油、黑芝麻。不像桌上那袋“梳打饼干”,大塑料袋装了十四个小塑料袋,每个小塑料装了四片饼干,还很诚实地写上食品添加剂,有一连串磷、氢、钠、铵等化学元素的字眼,一会石头偏旁、一会金属偏旁,看了心堵。
馓子盒上印了个图,老奶奶在做馓子,小孙女坐在一旁乐呵呵的。上面还有一首苏轼的《寒具诗》:“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苏轼在徐州任过知州,能为一民间小吃写诗,看来对馓子也很喜爱,还写出了点情欲味。但我对苏轼这首《寒具诗》有点生疑,因为我读过刘禹锡类似的《寒具》:“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嫩黄深。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虽只有数字之别,但后者读来更入味。
馓,零散的食物。因了“梳妆”的手艺,像妇人的发髻。和油绳不同,油绳是两根面团拧几下炸的,也叫麻花,小女孩梳的辫子就叫麻花辫。
徐州的馓子吃法很多,可以凉拌吃、泡着吃、卷着吃、炖着吃。小时候吃油绳倒是泡上开水加了红糖吃过,馓子我一直是用手一根一根掰了吃的。恰好,数日间去了山东、山西及徐州,桌上竟少不了一道馓子,再摆上蒜叶、葱、黄瓜丝、肉丝、西兰花、酱之类,甚至还有几片咸鸭蛋,都是用面皮卷着吃的。我也学着卷了,有仪式感,味道还真不错。
不过,馓子我还是喜欢一根一根掰着吃,感觉在数着我的小时候。我的孩子也像我这样吃馓子,一边吃一边翻着新买的书,每页都有个油腻腻的小指纹,想提醒他几句的,还是算了吧,我都活到了能背陆游《西窗》诗“看画客无寒具手,论书僧有折釵评”的年龄,也挺无聊的。
(散文均收入2021年7月出版的散文集《旧雨》)
四、名师点评

结对名师:夏坚勇
夏坚勇,散文家,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好的文章,原本就该是一种手工产物
读了这本题为《旧雨》的散文集,知道了他个人生命史的大体脉络。当然,读一个人的散文,并不是为了探究他的家世和交游。眼下我读《旧雨》,最大的收获就是常常有灵感的萌动。这就好比一个食客,吃着吃着就有了自己下厨的欲望。这不是说自己比厨师的手艺好,而是因为就这些很普通也很熟悉的食材,自己却从来不曾做出过这么好的味道。这说的是做菜,再说文章。《旧雨》每每触发了我心底那份旧日的乡村情感,但偏偏自己又从来不曾这样表达过。这大概就是所谓“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吧。说“人人”可能绝对了,应该说“很多人”,我就是“很多人”中的一个。以我的阅读经验,这是好文章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才气型的作家往往喜欢炫示华彩,但他却钟情于故乡炊烟下的家常味道。据说沈从文晚年喜欢用“家常”二字来评价作品,认为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旧雨》虽说不上却扇一顾倾城倾国,却蕴藉、温存,流溢着清新质朴的诗意。一个作家即使著作等身,也即使写到三百岁,但写来写去,还是走不出童年的那个村庄,因为那里是你灵魂的底色和归属。旧雨者,老朋友也。全书凡六辑,曰植物,曰动物,曰人物,曰旧物,曰食物,曰风物。此六物,皆老朋友也。我亦农家子弟,读这些篇章最能心领神会,亦钦羡于作者笔力抵达的深度和写作态度之真诚。书中所呈示的现场感、民间性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体恤,每每令我心折,亦每每勾起我的几缕乡愁。
而在读《馓子》一文时,我甚至产生了某种窥视欲。起初是惊艳于文章最后孩子留在书页上“油腻腻的小指纹”那样精妙的细节。后来一想,这是不是作者由灵感到诉诸表达的操作技法呢?作者或许是先从陆放翁的诗中得到了“寒具手”(会弄脏书画的手印)的灵感,然后设计出孩子一边吃饭一边翻书的场面,再辅以上文中已然铺垫过的“一根一根掰着吃”以及作者饱含人生况味的心理活动,整个场面就不仅气韵生动,而且极富于层次感。这样的推测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很可能不靠谱,但其中至少暗示了关于散文写作中如何张扬主体想象力的某种可能。文章是需要设计的,这就是匠心。在我看来,所谓设计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旧雨》是一坛风味醇厚的阳湖双套酒。双套酒这个词带有手工意味。好的文章——特别是散文——原本就该是一种手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