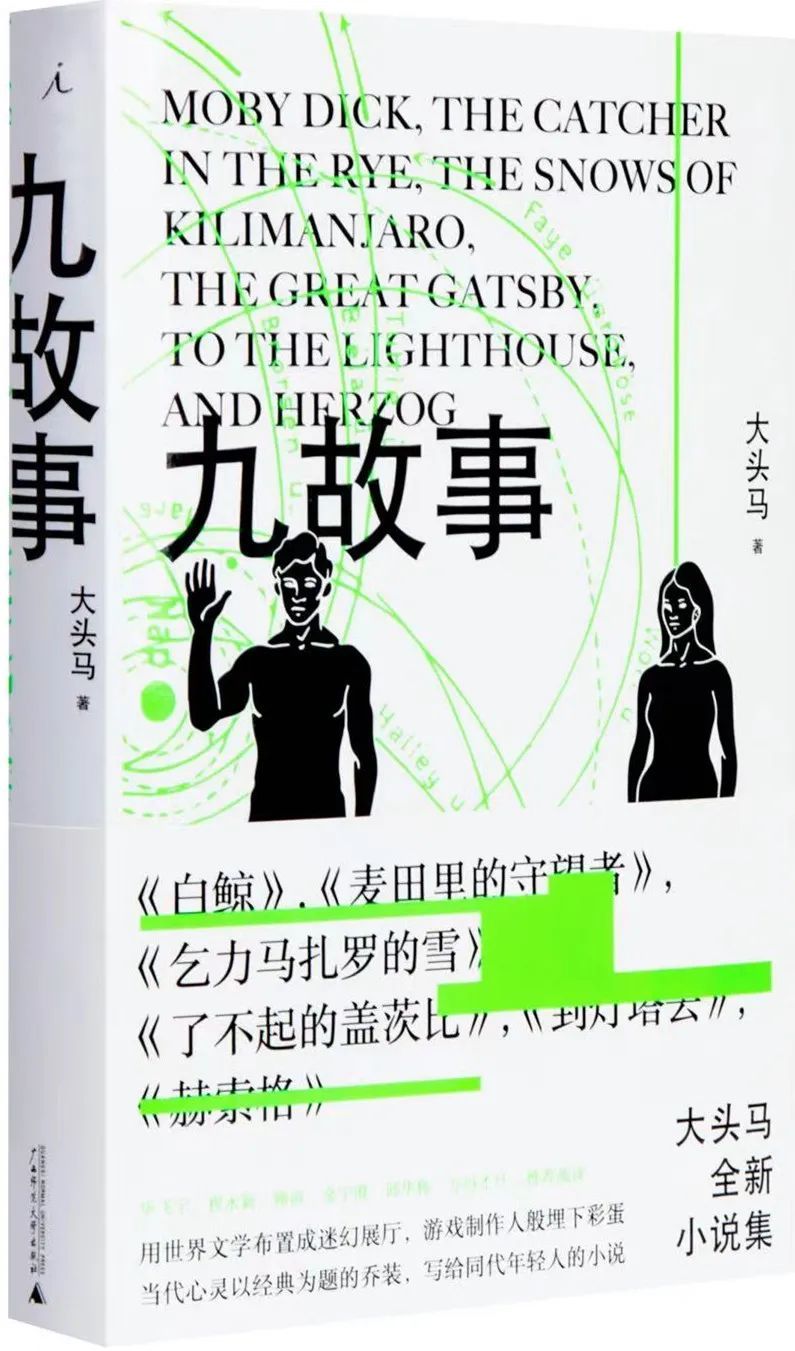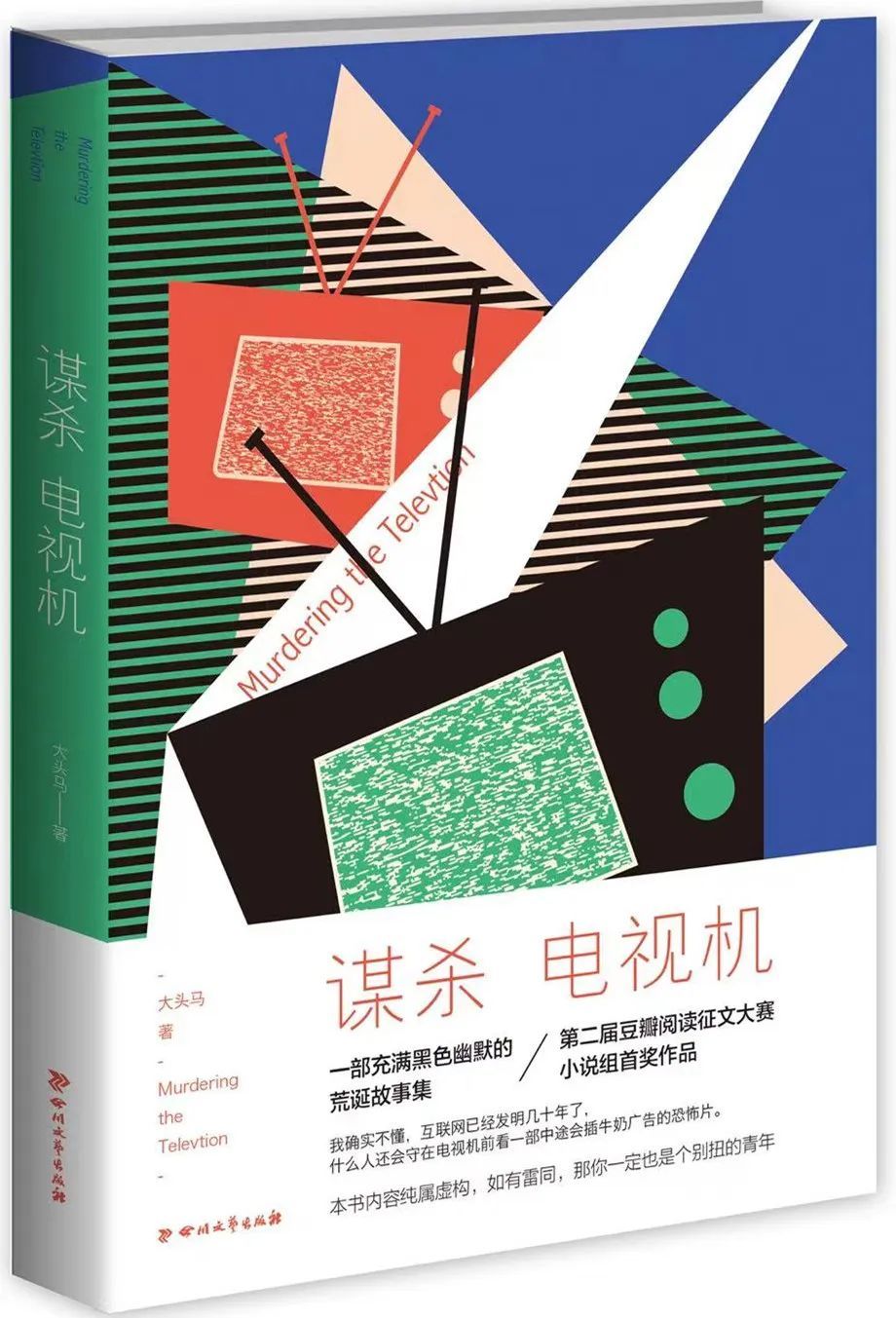开栏语
关注青年写作既代表了对当下文学现场的一种凝视,也代表了对文学未来的长远期待,青年写作需要在文学传统与时代历史、现实指向与精神维度、突破惯性与自我生长中不断拓宽内核与外延。即日起,江苏省作家协会在《文学报》开设“文学苏军新力量”专栏,邀请国内知名作家、诗人、评论家,对文学苏军中1985年后出生的、有创作实绩和创作潜力的年轻作家进行点评和推介,展现江苏文学的新生力量的同时,也促使他们的写作走向更成熟的未来。
第二期推出的是青年作家大头马,生于1989年,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九故事》《谋杀电视机》《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长篇小说《潜能者们》。
看,那个正在扮演“我”的人——大头马《九故事》
李振
“要想完美地演绎一个角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成为那个角色。”——这可能是罪犯,也可能是小说家,或者一个对所谓自我存有某种预设以及不存在任何预设的人。这不是什么人间真理,它只是故事,就像每个人都坚强又可悲地活在自己编织的故事里。大头马并不想在麦尔维尔的故事里扮演哪个角色,于是她造就了自己的《白鲸》。《白鲸》是“我”写给“万老师”的信。这本身就很可疑,我想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单方的言说更加笃定、从容也更加令人怀疑的了。这仅仅是叙述,你没法追究叙述本身的真伪,只有当它与故事镶嵌在一起,叙述才被赋予了语言之外的东西,比如它完成于审讯室,在一个经验老到的刑警面前。大概这就是叙述的魔力,只有当你沉浸于“万老师”的迷局才会发现,这其实是“我”和吴晶晶的故事。那个看上去稚嫩、人畜无害的实习记者为了“行使正义的权利和义务”成为警察,五年中“没有犯过任何错,破获过好几起大案要案,工作上尽心尽力”,却又如何实施了“完美犯罪”?小说只是剥洋葱般将犯罪过程一层一层地揭示出来,但对于犯罪动机始终闪烁其辞。然而一切都只是猜想,或者说是一种没有凭证的叙述——“我没有找到任何你犯罪的证据,我甚至没有资格要求你坐在我对面”——这甚至逼迫一个久经考验的老警察带着说不清的自我怀疑问出了“你究竟想做一个坏人还是一个好人”。“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它犹如一记重拳,清楚地提醒着人们这不是供词,而是小说。这是大头马的小说,也是“我”的创作,它是一个人真正进入某个角色之后对这个角色使命般的想象、创建、维护和讲述。从这个角度讲,“完美犯罪”和小说家的创造并无二致,他们都在寻找那个令人痴迷的角色并小心翼翼地融入其中,“真的这成了那个人”可能只是最大程度的相互成全。
扮演某个角色几乎成了大头马小说中挥之不去的心结。《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我还知道我不是在练拳,只是和这群朝九晚五每天下班后换上紧身衣的城里人一起,在这个商业楼盘地下最幽深最便宜的租赁场地里假装像个拳手”;《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我”为了一句无厘头式的谎言而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到灯塔去》里,我们说不清呆呆坐在电视机前和在赌桌上坚定下注的,到底哪个才是外祖母;《赫索格》里,女作家在酒精中发现了另一个自我而在酒醒后又迅速将其摧毁;《了不起的盖茨比》确实没让谁去扮演谁,但在童话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李。不得不承认,大头马在小说中促成了某种角色的狂欢,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试图通过种种方式跳出那个已然存在的身份或自我。但这只是扮演或伪装吗?就像“我”原本只是打算买一份报纸,却因为信口而出的谎言就开始了奔赴莫斯科的旅程。那么,在踏上列车的那一刹那,谎言是否还能成为谎言?如果说《白鲸》里的身份掩饰还有一个实施犯罪的动机的话,那么其他作品中的角色变换似乎更像为了扮演的扮演。但是,哪个是演员,哪个是角色,哪个才是所谓真实存在的那个人?这大概不仅仅是一个如何丰富故事情节的问题,它还包含着作者对于人和这个世界存在方式的辨析。扮演的和被扮演的以及整个扮演过程都是现实的,它真实地照映着人无法克服的虚无和同时无法抗拒的欲望,证明着那些被固定了的角色如水中倒影,而那些被虚构或想象的存在又是怎样坚不可摧。二者犹如硬币的两面,谁又是谁的因果或前提?更重要的是,这种被死死咬合在一起的现实,却以虚构的方式被讲述出来。那么,是不是唯有虚构才是通往真实的可靠途径?
大头马谈到《九故事》的命名时说,“我读这些小说的时候,会有这个小说叙述者的声音。当我去写自己的小说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脑海中的叙述者的声音,跟那个是重叠的或者是有共鸣的,它们无论是在意象还是气质上,或者仅仅是一种情绪上,会让我感到熟悉和亲切。”所以,当大头马用麦尔维尔、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名篇来命名自己的小说,用塞林格的《九故事》作为小说集的名字时,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致敬。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叙述上的期许,更准确地说是作者下意识里认定这个故事应该被怎样的声音讲述。这倒和大头马小说中的人物颇有一些相似,也许这时我们才能把整个小说集贯通起来。大头马对叙述本身似乎抱有某种特别情结,这不仅体现在她对语言和叙述方式的拿捏,还包括作家让叙述的秘密直接介入到故事的架构与推演之中。从这个层面来看,大头马的《九故事》实现了一次放纵的心灵独白,她带上面具,却演绎出最真实的故事。无论叙述者还是小说人物,一时跳开了具体身份和现实生活的束缚,犹如一场满是荒唐和隐喻的实验话剧,用舞台上放肆的大笑来诉说内心深藏的苦楚,用谎言来诠释现实生活的真实。这是沉浸于生活伪装中的人以另一重伪装发起的一场反攻,是被设计或虚构的生活悉心埋伏下的“现实呈现”。角色被扮演、谎言被编织,正如真相也需要被讲述。真实从来不是小说的第一要义,小说的虚构作为一种颇具悲剧色彩的努力,在人们所必须面对的绝对虚无之上建立起某种相对的永恒。它不仅在小说的逻辑中摆脱了虚无的困扰,而且随着语言、叙述、文本转变为能够直接介入人们精神世界的力量,在生活的尴尬与生命的虚无之外为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因为即便作为“谎言”,它也正塑造着现在的人,或许又将改变之后的生活。
(本文作者为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谈
找到小说的活法儿
大头马

我大概是从2012年左右开始写小说。准确地说,不能叫写小说,是学习写小说。直到现在,都还在学习的过程,老实讲,经常感觉到自己不会写。所以我特害怕写创作谈。打开文档,大脑总是一片空白。
前一阵参加一个小说笔会,是评论别人的小说,我突然想到一种说法,什么样的小说才算是真正的小说呢?有时候看自己的一些作品,别人的一些作品,我会直觉那不是小说,到底为什么不是,也说不上来。当然,针对自己的作品,我可以直接说那是写废了,可别人的作品,总不好说得这么直接。那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那些看上去不像小说的小说,是没有活过来的小说,好像一个机器人,有头有身体有四肢,也穿着衣服,会动,看着像人,可不是真正的人。言而总之,缺乏人的灵魂。
每个小说都有自己的活法儿。这里面既没有固定的路径,他人的活路也无法复制。每一篇小说,都得找到自己的活法儿。我最近在想,为什么我感到写小说越来越难了?那恐怕就是我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自己写作的不成功,尤其是那些具体的失败。在最开始学习写小说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模模糊糊地遵循着两个路径去写,第一是模仿,第二是自我表达。这是两个大概的方向和驱动力。那时,自己对小说的认知也是极为模糊的,也就是说,根本无从分辨小说是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那么对于自己的要求,也就较为放松。总觉得一篇小说只要完成,看着想那么回事,就算是“小说”了。而现在,我越来越能感觉到一篇小说缺了一口气,那样的小说就是死的,就不能称其为小说。
有一天晚上失眠时,我又在琢磨这件事。我想写小说真是太难了。我虽然已经能意识到活的小说和死的小说之不同,可究竟是哪些具体的因素让小说活起来,我仍然说不太上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许是很多人所说的“完成度”?完成度99%,甚至无限接近100%时,小说都没有活。一个小说有其活起来时应当的面貌,叙事、风格、节奏、主题等等,任何一个细微的部分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时常也和完成度无关。完成度似乎旨在说明一个小说各方面需做到平衡,同等的完善,让一个小说看起来不至于顾此失彼,与理想状况相差不远。但也有不少小说,因某些方面的特点太过优异显著,使得小说也活了起来,不仅活了,还因其不同寻常的活法,创造了灵魂崭新的样貌。
回头去看,原来我尝试写小说也十年了。截至目前,我出版了四本书,写了几十篇小说,这里面活起来的小说,我估计屈指可数。得修正一下开头的说法,前面很多年,我只能算是尝试写,都不能叫学习。学习是一个有意识的、有方法论的过程,也就是在近两三年,我才开始有这个主观意识。关于我自己的活法,也还在寻觅,希望能快点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