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自己的作品里看到另一部经典作品的影子,就不算上乘之作,甚至是一次失败的写作。这很难,但我心向往之
贺绍俊:本夫兄好。
记得最初读到你的长篇小说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时,有一种惊世骇俗之感,就觉得你的写作完全进入一种挥洒自如的神奇状态,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细想想,你骨子里大概就有狂野奔放的因子,这些因子平日蛰伏不动,一动就石破天惊。纵览你40年来的创作,这种因子不时在你作品中闪现,熠熠生辉。60岁以后,你完成《地母》三部曲最后一部《无土时代》,获《当代》文学奖,并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和国六十年典藏”。70岁以后,你又井喷一样写出《天漏邑》《荒漠里有一条鱼》两部长篇巨著,入选各种好书排行榜,并分别获得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施耐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在你这里,年龄不仅不是问题,还让你达到创作的巅峰。从写作方法上看,你娴熟运用了现实主义写作和现代派手法,甚至在同一部作品里自由切换,时有神来之笔。从内涵上看,你以比年轻时更加犀利的笔锋,更加深邃的思想穿透力,用奇异而又艺术上可信的故事和人物塑造,对人与自然、人类文明、人性、生命、道德伦理等重大命题,撕开来深度解剖和阐释,直击痛点,让人产生强烈心灵震撼,颠覆了许多固有观念和认知,让读者获得巨大的阅读快意和疼痛感。这样的故事、人物、场景在你过去的小说里时常出现。《荒漠里有一条鱼》是又一例证,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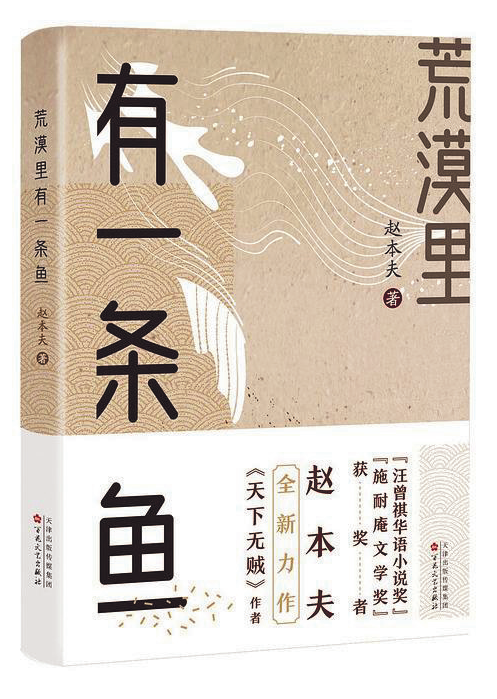
这么多年,文学浪潮一波接一波。但看得出,你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抵触一切新的思潮,而是观察思考,淡定从容,一直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因此很难把你归类到哪个潮流或哪个流派中。尽管总在潮头上看不到你,使你的作品少了一些聚焦和一时风光,但大浪过后,泡沫消失,发现你的作品沉甸甸仍在那里。但凡读了你的作品,都会惊异它的分量和与众不同。你把厚重和轻灵、粗犷和细腻、笨拙和诡异、浅显和深邃、传统和现代这些互相矛盾的东西融为一体,毫无违和感,显示出深厚的功力。汪政先生说,“赵本夫的高古、质朴、苍莽和野性,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阎晶明先生有感于你短篇小说的纵深感,认为你在短篇小说创作中“有文体学的贡献”。陈思和先生在多次评论中,把你看作新时期以来亚文化写作的先行者。何镇邦先生在一篇评论你《无土时代》的文章中说,“和赵本夫同时代的作家大多已经见底,赵本夫却依然混沌。”吴俊先生干脆把“中国作家赵本夫”作为他一篇评论的题目,等等。我完全同意他们这些意涵深刻的评语。你的这部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是又一部史诗性大作。众多评论家已有不同视角的解读和精彩评论,给予极高评价。我也写了专题评论文章,并在《文艺报》的《五年来长篇小说巡礼》一文中,对这部作品作了重点推荐。我认为《荒漠里有一条鱼》“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开创新纪元的大寓言”。关于寓言,我们稍后再谈。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种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的野心,一直是你的自觉追求吗?
赵本夫:谢谢绍俊兄多年来对我作品的持续关注。
新时期以来,主要是前20年,文学浪潮一波接一波。于是我们看到,每次文学浪潮到来,先是出现一两篇有代表性的作品,接着冒出一批类似的小说,形成一个所谓流派。应当说,这是一个文学并不成熟的阶段,但也是一个不能超越的过程。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大家的视野,特别是一些经典作品,让人眼界大开,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于是争相模仿、探索学习。这实际上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发展。但这种状况不应长久。如果满眼都是仿品,中国文学是没有前途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兼任《钟山》主编。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思考,我提出“原创、拒绝、远行”六个字的办刊方针,把这六个字醒目地印在杂志封面上,并在同期首页写了一篇小文《名山寂寞》,阐释这六个字的办刊理念。“原创”二字就是希望文坛在经过十几年的学习、模仿之后,出现有中国气派和深刻内涵的原创作品,《钟山》将予以大力推出。“拒绝”二字有点扎眼。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讲包容,刊物通吃作家,作家通吃刊物,致使所有刊物都大同小异。如果这样,全国有一家刊物就够了。我希望每家刊物都有一个不同于别家的鲜明特色,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家群和读者群。如此,众多文学刊物会“面目全非”,将是一个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繁荣局面。刊物在选择稿件的时候,想包容一切是不可能的,一定有所选择,选择就意味着会有拒绝。在这里,选择和拒绝成了同义语,而拒绝也许更能凸显文学的个性。在刊物和作家之间,拒绝是平等的,刊物可以拒绝作家,作家也可以拒绝刊物。唯一的理由就是:你不适合我。当时的《钟山》已是名刊,并不缺少稿源,包括很多名家都愿意把作品交《钟山》发表。我当时给编辑部开会,告诉编辑说:“你们的任务不是组稿,是退稿。”不管是不是名家,不适合在《钟山》发表就要转退。后来《钟山》编辑的确退了不少名家的稿子。其中最不好退的稿子,则由我亲自写信或登门退稿。至于“远行”二字则很好理解,就是希望由《钟山》发表的作品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具有久远的生命力。《钟山》这六个字的办刊方针,得罪过一些朋友,但有更多的作家和读者来信表示理解和赞扬。后来,柳萌先生在《文艺报》、黄发有先生在《当代作家评论》,都曾专门撰文,对这六个字办刊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为了保证办刊质量,不发人情稿,我当时还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以身作则,不在《钟山》发表我的作品。因为我还在作协担任职务,因此也不在《雨花》等江苏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至今30多年了,我没有一篇小说发表在江苏文学期刊上。
《钟山》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潮流,应负有引领的责任。它对别的作家具体产生过什么影响,无从得知,但起码让我个人的创作,保持了一份沉静和清醒。在中国作家的书房里,几乎都有一个外国文学专柜,那些作品,大家都看过。对中外文学经典包括国外现代派经典之作,如果仅仅是一个读者,敬佩之下,尽可反复阅读,顶礼膜拜。但如果是一个写作者,惊叹之后,不是去盲目模仿,而是应尽快逃离,不需要把马尔克斯、卡尔维诺整天挂在嘴上。那时,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追求作品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如果在自己的作品里看到另一部经典作品的影子,就不算上乘之作,甚至是一次失败的写作。这很难,但我心向往之。
对作家来说,生活中可以有很多朋友。但在文学之路上,不应成群结伙,勾肩搭背,只能孑然独行。也许前程一片苍茫,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寓言富有张力,会让人产生联想,回望来路,知道当下和未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贺绍俊:《荒漠里有一条鱼》有着鲜明的寓言性,我认为它是由两大寓言组成的。第一个寓言是一条大鱼的寓言。这是一条曾经游弋在黄河里的鲤鱼之王。传说鲤鱼之王能活百年千年,大河里所有的鲤鱼都是它的子孙,黄河突然决口改道,把这条鲤鱼之王搁浅在荒漠一片沼泽里,靠鳃边一团泥浆艰难地活着。在中国民间文化中,鱼一直被视为一种祥瑞之物,中国人对鱼的崇拜历史相当久远,在五千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上,就绘有大量精美的鱼纹图,可以想见在远古先民的心目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分量。学者认为,古人之所以崇拜鱼,主要原因是鱼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这是一种强烈的生殖崇拜。小说中最先出现的渔夫老八,你写他爷爷曾两次见到过正在巡河的鱼王,这是一件大吉祥的事,于是这个家族就有了超强的繁殖能力。老八和两任妻子生下二十一个孩子,大家惊呼他“快赶上鱼王撒籽了”。黄河决口后死里逃生的老八,在荒原上发现了搁浅的鱼王,不仅救了它,还建了鱼王庙、鱼王庄。从此,不管鱼王庙还是鱼王庄,都把生殖当成头等大事。
第二个寓言是关于生存的寓言。鱼王庄的乞丐们为了活下去,一代代人在荒原上栽树,改变生存环境,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每年饿死、累死、冻死的很多人,会被就地埋进树坑里,所以鱼王庄没有坟墓。但在每一棵长得特别茂盛的树下,一定埋着一个乞丐的尸体。如此决绝的行为感天动地。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人。而鱼王庄的后人,很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因为外出讨饭的女人,为了一口饭,或自愿或被迫忍受陌生男人的侵犯。到年底时,只能挺着大肚子回来。她们忍着莫大的屈辱,千里万里爬冰卧雪,都必须回来,因为她们要在开春时栽树。栽树就是鱼王庄的法律和信仰。鱼王庄没人鄙视她们,更无人责怪她们,重要的是女人们都回来了。她们带回来的孩子,不管是谁的种,都是鱼王庄的后代。这种对生命的珍爱,是超越血缘、超越伦理的大爱。生命在延续,栽树后继有人,这就够了。其实,他们自己看不到也享受不到荒漠变森林的福祉。但他们知道,只有栽种树木,才能修补破损的大地,让后人生活在绿荫下。这种生存意识和大自然紧密相连。
寓言一直伴随着你的小说写作,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这一点。我为《荒漠里有一条鱼》专门写的评论中,也称这部小说是从一个生殖到生存的现代寓言。不知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你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写法呢?
赵本夫:是的。我同意你的分析。这部作品之所以要采用寓言化的写作,是因为寓言像隐言,可以包藏很多东西。生殖和生存都是生命延续的根本要求,它和自然界所有生命一样,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属性无限增长,人的自然属性越来越淡薄。但人类终是自然之子,离开大自然,一刻也活不下去。看轻自然属性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会带来严重的恶果。比如我们看到的,越是所谓文明程度高、越是繁荣富裕的社会,人们越是不愿意生育,甚至不愿意婚配,只看重个人的当下享受,或被繁重的社会性、家庭性事务所累,谈“生”色变。于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老年社会,人口开始萎缩,并且不可逆转。当人类生殖意愿开始降低的时候,不管科技发展如何日新月异,不管经济多么发达,不管文明程度多高,这个自然界的人类物种,事实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拐点。在《荒漠里有一条鱼》中,鱼王庄、鱼王庙把繁衍后代、接续生命看得如此重要,正是源于生命的本能。这里人没有那么多的社会性,更多的是自然属性。他们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虽然贫困到一无所有,却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主人公老扁从少年时代,就窥探到了鱼王庙求子的秘密,但他不敢说出去。等他长大当了村长,就不能说出去了。因为生殖已成了鱼王庄和鱼王庙的生命宗教。鱼王庄人把生存和修复荒原、植树造林联系在一起,当然是现实生存的需要。但他们并不知道,人对树木的依赖和感情,来自古老的记忆。在上古时代的“五氏”中,有巢氏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排在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前头的,为“五氏”之首。《庄子·盗跖》篇曰:“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是说,我们的先人正是从树木上下来的。树木曾是人类避险处和栖居之所,像母体一样重要。也许,鱼王庄人并不知道上古人类的故事,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对树木的依恋和亲近,早已储存在血液中。就像我在另一部小说《无土时代》卷首语中题写的一句话:“花盆是城里人关于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道理是一样的。
生殖和生存的法则久远而严酷。寓言富有张力,会让人产生联想,回望来路,知道当下和未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贺绍俊:我觉得你钟情于寓言的叙述,是因为寓言相对于单纯讲故事,能够更好地表达思想。你的小说虽然故事情节性很强,但同样有表达思想的强烈冲动,所以我说你是一位思想家。就像你的《荒漠里有一条鱼》里的两个寓言,都有对生命的思考,生殖和生存两大命题,都是放在大自然的背景下看待的。你对生命力特别看重,所以你所欣赏的人物往往都有强大的生命力,有顽强坚韧的品格,甚至具有一种野性。哪怕是老扁这个看似丑陋、弱小的人物,其内心的强大都是无法想象的。哪怕你写女性,也有一种内在的阳刚,比如《无土时代》中的柴姑、小迷娘,《天漏邑》中的七女、檀黛云,《荒漠里有一条鱼》中的梅子、草儿、七月、杨八姐、秋月等等。她们性格各异,充满女性的魅力,但她们都是有担当的女性。是不是你希望你所欣赏的人物都有强大的生命力?你塑造这些人物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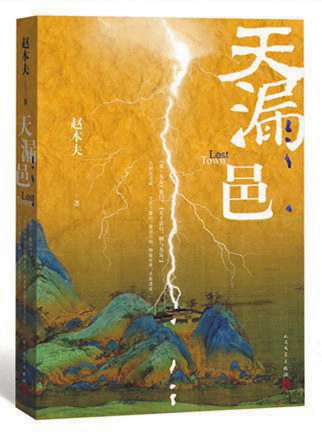
赵本夫:我是一个忠诚的大自然崇拜者。我们一直认为,人类文明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文明。这是人类托大了,蚂蚁听了都会偷笑。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人类文明只是自然文明的一部分。人类出现不过几十万年,蚂蚁已有上亿年历史。一棵树可以活几百年上千年,一簇小草可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人生不过百年。无数自然界的生物远比人类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所以人类才有了仿生学。如果把大自然扩展到茫茫宇宙,人类就更显得渺小无知。大自然的奥秘神奇不是人类可以刨根问底的。几千年来,人类总想把什么都搞明白,但至今也没有搞明白几件事。人类总说,让大自然为人类服务,结果成了大自然最大的破坏者、掠夺者。特别自工业革命以后,短短二三百年的时间,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已远超过去的几千年,地球已是千疮百孔。在《荒漠里有一条鱼》中,乞丐们要求甚少,但他们在做修复大地的壮举,一代又一代。这才是人类应当做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是原始崇拜,也必然是终极崇拜。莫忘初心啊!
人类的确创建了自己的文明。所谓文明,简单来说,相当一部分就是有形无形的秩序和规范。这当然是必须的,不然会天下大乱。但群体秩序和个体生命如何平衡,是一个永远的话题。我在《地母》三部曲中做过一些探索。在第一部《黑蚂蚁蓝眼睛》中,我写了文明的断裂,黄河决口后,无数村庄毁灭,人被淹死,文明秩序不复存在,土地没了主人,也不再是谁的财富,而重归洪荒,万千生命如何汪洋恣肆。第二部《天地月亮地》写文明重建过程中,生命的扭曲、痛苦、挣扎和无奈。第三部《无土时代》是对文明的追问,写城市中脱离了大地自然的人们,患上各种“城市文明病”,特别是精神的萎缩。的确,我一直在作品中呼唤强大的生命力乃至野性。野性保存了生命的原始基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我们今天保护普氏野马、蒙古野驴、西藏野牦牛、亚洲象、藏羚羊、东北虎,以及众多野生动植物。比如袁隆平搞水稻,一定要找到野生水稻杂交,等等,都是为了让动植物保持蓬勃的生命力。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只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让文明充满人性和活力。如果人类把秩序和规范变成枷锁,让人动辄得咎,让人蔫头蔫脑,让生命个体失去活力,文明也必然萎缩,而人类的前景也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岂不悲哉。

他们用生命换取生命,用死亡逃离死亡,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梦想
贺绍俊:塑造人物很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在《荒漠里有一条鱼》中,你塑造了五十多个人物,包括小人物在内,每个人物都很出彩。我想请你谈谈主要人物老扁,因为这个人物在文学画廊里非常少见。你认为人物塑造在现代小说创作中仍然是重要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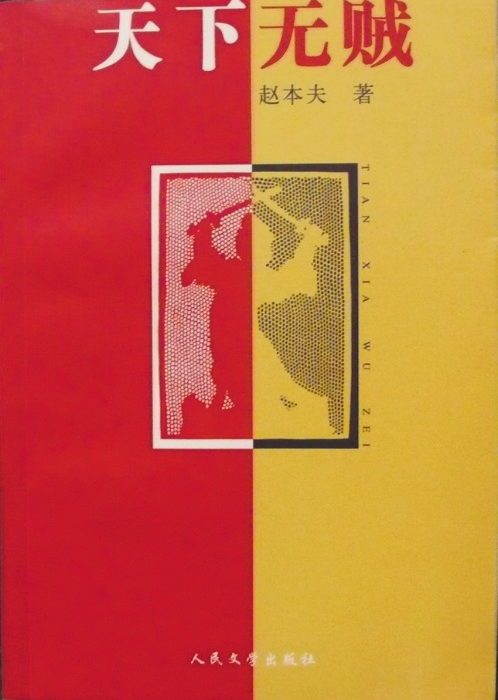
赵本夫:塑造人物在传统小说中极为重要,在现代小说中依然是骨架。因为人物是小说内涵的载体。老扁这个人物身单力薄,貌相丑陋,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信念,这就是把荒原变成绿洲。为了栽树,他挥一根皮鞭无情抽打被饥饿、寒冷、疾病折磨得倒下的乞丐们,让他们爬起来继续栽树,死了人当即埋进树坑,然后吆喝着继续栽树。他每天用皮鞭打人,也经常被乞丐们夺过鞭子按在地上抽打,打得满头满脸都是血。但打过后,乞丐们又把鞭子交还给他。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个挣扎在生命极限的村庄,需要一个好人,也需要一个恶人,这个人就是老扁,不然什么事也干不成。为了阻止日军毁掉几十万亩树林,他被迫把新婚妻子草儿推送给日本军官龟田。这是一次屈辱的交易,也是一次艰难的选择。最终树林没能保住,妻子也疯掉了。乞丐们恨不得杀了老扁。可他全然不顾,一边怀着深深的愧疚照料妻子,一边又吆喝乞丐们重新栽树。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树林一次次被外人毁掉,他就带领乞丐们一次次重新栽上。每年春天过后,全村人要外出乞讨,他利用村长的职权,为所有人包括逃亡来此隐藏的地主分子,都开一个贫农成分证明信,方便他们在外谋生。每年腊月,乞丐们带着回家的喜悦,带着在外的伤痛和屈辱陆续归来,老扁总会冒着刺骨的寒风,站在村口的雪地里迎接他们。如果少一个人没有回来,他会立刻派人或亲自去外地寻找。少女秋月因在千里之外被人强奸而报复杀人,被判死刑,老扁带人连夜赶去,全力营救,终于没能如愿,还是捧着秋月的骨灰回来了,全村人到村口迎接,哭声震天。对于老扁,乞丐们恨他、诅咒他,又服从他、尊敬他、崇拜他。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矮小的当家人太难了。当树林又一次被外力毁掉,妻子草儿自杀时,这个已经衰老的男人终于支撑不住,崩溃自杀,追随亡妻而去。几十年间,他在用鞭子抽打别人的同时,也一直在抽打自己的灵魂。那是一种煎熬。但他死不瞑目。很多年后,当他的灵魂重回鱼王庄时,看到荒原终于变成无边的大森林,老扁哭了。塑造这个人物是困难的,评价他同样困难。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说过一句话:“我欣赏那些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却依然泪流满面的人。”我只能说,老扁就是那个依然泪流满面的人。
中华民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我们并没有总是辉煌,也有过艰难和屈辱的时候。老扁和鱼王庄人的艰难和屈辱只是一个缩影。我不想回避。只有正视它,并敢于说出来,就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展示的那样,才是真正的强大。事实上,鱼王庄人屈辱而没有屈服,沉默也不是麻木。他们用生命换取生命,用死亡逃离死亡,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梦想。
贺绍俊:你有很强的写实能力,小说中的细节描写都很真实生动,这是一种现实主义写作的基本功。有些作家只玩现代派技巧,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基本功,无法将细节用文字描摹下来并让人读了能被吸引和感动。你同时又有超强的想象力,你的小说完全不是刻板的现实主义,而是包含很多非现实的东西,神话、寓言、象征、荒诞,都是你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40年来,当代文学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有单一写实性的、刻板的现实主义文学。现在的小说叙述,写实与非写实,现实性和非现实性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这是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携手共进的时代。但我觉得,你小说中的非现实,并非从国外现代主义文学那里学来的,而是来自民间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荒漠里有一条鱼》里讲的是非现实的故事,却具有内在的现实主义品质。它一看就不像西方现代主义的文本,而是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的韵味,可以让我们联想起中国民间的神话传说,或者像《山海经》这样的古代典籍。不知我的判断是否准确,我很想知道你在采取非现实的叙述方式时,有什么体会和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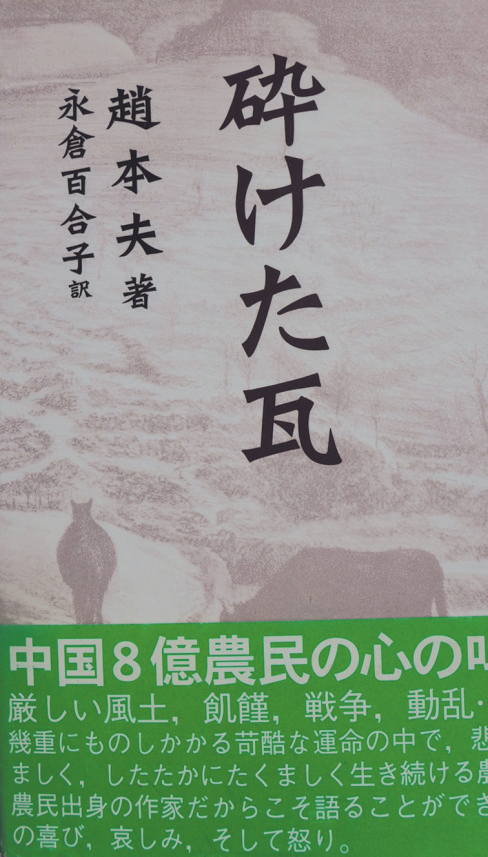
《碎瓦》日文版
赵本夫:你说得很对。东西方文化各有各的辉煌。我也曾走马观花,先后去过西方20多个国家,读过世界通史、西方军事史、西方美学史、西方美术史、西方文学史,以及西方每个时代的代表作。就像一个旅行者,走过千山万水,领略过各种风景,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回家。中国文化才是我的根脉。因此,我在写作时,并不会参考西方现代主义文本,恰恰相反,我会竭力避开。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混沌、包容、博大、神秘,仅在数千种古典志怪传奇、笔记小说中就有充分体现,那几乎是一个汪洋大海。在这些作品中,充满对山川河流的尊崇,对封建礼教和腐朽传统的忤逆和戏弄,对人性的大胆展示,充满生命的活力,其想象力更是匪夷所思。对作家来说,营养足够丰富。所以我的作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一种自觉追求。可以说,《荒漠里有一条鱼》是一部向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上古神话寓言致敬的作品。其实这些上古神话寓言,都可以看作是小说,且都是小说神品。无论其人物、故事、精气神,全都有了。寥寥数语而传千秋万代。今天的小说家有谁能超过它们吗?“五四”以来很多作家批判国民劣根性,产生了很多经典作品和人物。我早年也写过一些这类小说。但文学不应到此为止。如果仅有封闭、麻木、愚昧这些东西,中华民族走不到今天,而上述远古神话寓言才是民族精神的真正母体:经天纬地、志存高远、忍辱负重、不屈不挠……《荒漠里有一条鱼》充满了苦难,正如那条黄河巨鲤在泥沼中遍体鳞伤,活得如此艰难。但我不想让作品充斥着沮丧、抱怨、嘀嘀咕咕、灰头土脸、滑稽可笑。明代大医学家张景岳在诠释《黄帝内经》时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我想写出千里荒原上升起的那一丸红日,以及乞丐们身上的那一息真阳。我想我做到了。
东西方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文学作品有所不同是自然的。我们应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我曾经说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作家应保持一点矜持,不必刻意寻找认同感。认同当然很好,不认同也许更好。异质才是文学的生命,世界因不同而五彩缤纷。如果卢浮宫和故宫一样,我们还会去看吗?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