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望子访谈:我关注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变得复杂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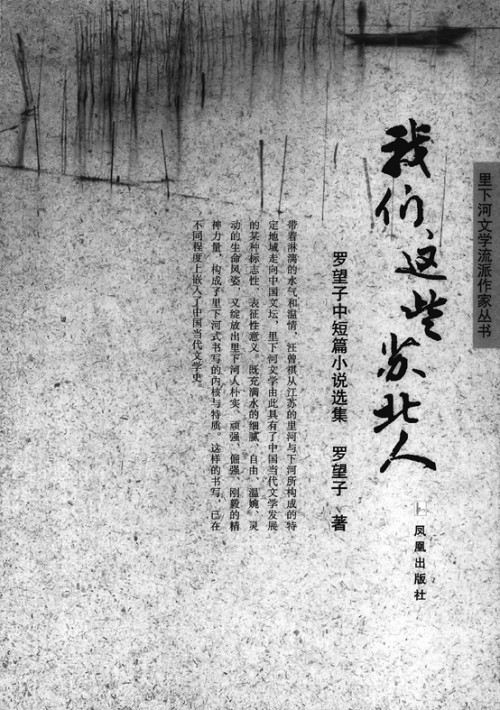
罗望子简介:原名周诚。江苏海安人。著有长篇小说《暧昧》、《在腼腆的桥上求爱》、《梅花弄》、《人人都想坠入爱河》等,其中有多部以故乡为题材。——罗望子访谈
孙(孙小宁,著名文化记者):一个基本地理问题:你出生在海安,这是里下河的哪个区域。你的小说其实很少出现里下河这样的字眼,而更多是苏北人——我们这些苏北人。苏北、海安、里下河,在你生命中,是怎样的关系?
罗:海安确是有几个乡镇属于里下河区域。应该是里下河的东南缘地带。我出生在海安的东北角,和评论家汪政、吴义勤、王尧、何平,作家鲁羊,诗人小海的家乡邻近。我的那个村子就叫高墩,隔河就是东台地界。每年夏天,里下河流域涨水的时候,防洪排涝是政府的头等大事,里下河的水从我家屋后的红星河汹涌而过,印象特别深刻。
苏北是相对苏南而言,尤其是上海人,统称我们是苏北人,以前都喊我们江北佬。实际上海安居于苏中枢纽地段,拥有五个高速出入口,新长线和宁启线在此交汇,也是新开工的沪通动车的终点,更别提历史悠久的河运了。
我是从与上海隔江相望的海门调回海安,再调到省作协的。但我一直住在海安,除了家庭情况,更多的是意识中,搬到南京并没有多少优越感,反而会像驻守孤岛。某些程度上可以说,方言就是地理。我喜欢本乡本土的语言,亲切,幽默,不失乡野之趣。也许就是这些因素,造就了我开放的心境吧。
孙:“里下河文学”举的是汪味小说之旗,但我在你的小说里,很少能闻到这样的汪味。连水气都闻不到。人和人之间,内里还有一种紧张。如果你也认同自己是里下河作家群中的一员,你希望给里下河的书写带来什么样的新的经验?
罗:我被打入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史册,可能不是作品风格,更多的是地理因素的考虑吧。我也乐意做这样的一个异数。在里下河众多的作家当中像我这样留守的并不多。我经常出没于里下河的小县城和村庄,和那里的朋友交往。大家玩得很投入。在我看来,里下河作家的文学书写,不能看作仅仅是书写里下河,更不能止步于乡土。里下河作家不仅仅要思考和表现对传统的乡村伦理应该怎样的挽留和鉴别,对珍贵的乡村情感应该如何继承和重建,更要注重的是对乡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怎样的乡土馈赠。
孙:《我们这些苏北人》应该是你的故乡系列小说集。同名的这一篇我非常喜欢。里面父亲兄弟俩几十年的恩怨,以及整个家族的微妙联系,既有乡村伦理的再现,同时个人史中也能看到中国进程的某些瞬间。冒昧地觉得,它是你的故乡系列的交卷之作,你写它,其实是对自己的来路有个交待,但还是要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中途写这样一系列的故乡题材?因为你自己发言中也说,最早是写都市题材的。
罗: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一波三折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先锋作家如此,新生代作家亦如是,一个人的成长更是如此。2003年,李洱就在《收获》发表了关于乡土中国的交卷之作《龙凤呈祥》,突显了乡村伦理在乡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我的转型已经大大滞后了。我似乎被看作是先锋性比较强的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我一直在酝酿要有些改变,也可以说过去的写作走到了一个瓶颈期。于我而言,故乡也好乡土也好,并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形象,他是母亲,也可以是父亲,是他们脸上的皱纹和乡音里流露出的内心世界。2008年我写了短篇《墙》(《收获》),2009发表中篇《我们这些苏北人》(《江南》)和短篇《吃河豚》(《收获》),它们是对乡村伦理的圆廊式再现。《吃河豚》写的是一群教师朋友(也就是乡村知识分子)十年后的相聚。《墙》写的是我的兄弟之间的较劲,《我们这些苏北人》写的是我的父辈之间的纠葛。可能把他们倒过来读更能理清乡村伦理的流变。事实上,《我们这些苏北人》在《墙》前面早就动笔了,写起来则要慢得多。当时我的想法,乡村经验就是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也必须用中国故事的方式来讲述。中国讲述就是工笔写实,但我拒绝一地鸡毛式的写作,也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要被写实所捆绑。
孙:虽然你身处海安,没有离开故乡,但我感觉吸引你更多的是:乡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变得更复杂的人。小说《故乡》的主人公,从故乡到都市打拼成功,退回故乡,最终又消失于故乡。这个人的进退,最能折射出一个有故乡而故乡已不再是原有故乡的当下人的处境。你的“苏北”,的确有大量的现实信息。已经不是汪味“里下河文学”所能涵括。
罗:关于故乡的答案就像星星点灯,可哪里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呢。城市化进程造成的荒诞奇观和乡村颓败,已经使故乡显出荒谬的一面。以后,恐怕只能从地名学的知识谱系里去寻找故乡了。至少90后们是没有故乡的。没有故乡说白了是没有多少童年的记忆。三口之家的主体模式和离异家庭的大量涌现以及应试教育的条条框框,使独生子女们普遍自闭冷漠。那些乐观开朗自信有爱心的孩子,倒反而是家里住有老人三代同堂家庭的孩子。这恰恰印证了“家有一老是个宝”的乡村伦理。这时你会发现,乡村经验中那些珍贵的部分在默默抵抗和祛除着当代社会的重重危机,默默教化着下一代。这正是我要关注的地方。
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那么,我就要关注你所说的“乡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变得更复杂的人”。这才有了我的新乡土小说,诸如《伴娘》《珍珠》《故乡》等,这些作品中的笔下人物,虽算城镇新人,但都怀揣着乡村经验。我感兴趣的就是他们怎么样让乡村经验在城市落地生根,尽管都是不自觉的行为,他们事实上不仅传播扩散着乡村经验,而且在新的群体和环境中,还不断修正改写着乡村经验。在《我们这些苏北人》这本集子里,除了《蔡先生》是向汪曾祺先生的致敬之作,我有意识地收选了我所谓的这些新乡土小说。表面上我又在重写都市题材,而实质上与以往的城市写作已经有所不同了。
孙:鲁敏说,无论一个作家写不写故乡,他的作品里都会有故乡的胎记,那你的胎记是什么?
罗:我永远是个乡下人。就像贾平凹说“我是农民”一样。胎记必须有,我的胎记还不只一个。“父母在,不远游”算不算?亲戚们有事就找你拿主意算不算?其实故乡的人和事,细节与地气,对我都有影响。这么说可能有些扩大化,但的确是我固守小县城的原因。
孙:里下河风景很美,很多作家笔下都会刻意强化这种地域色彩,我感觉你并不想把它们处理成纯美风情画。可能在你身上,外国作家的影响要大于里下河那些名作家。但你肯定心里又是有汪老在的。这两种影响在你身上怎么调和?
罗:我想每个作家都不会去刻意调和这样的影响吧,就像我不会太在意我是不是里下河作家一样。60年代出生的作家,目前应该是最重要的文学力量。这一代作家生于文革期间,成长于改革开放,成熟于新世纪。他们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每个人成长的经历和环境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眼光已不再局限于东西方的文化或文学某一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他们的身上,都携带存贮着乡村伦理的情感密码。我可能受外国作家的影响大于中国作家,但我仍然是在用我对文学对乡村的理解在表现生活,在建立一种“想象的真实”和“想象的历史情境”。说到汪曾祺先生,我觉得他是个会玩善玩、并玩出境界的人。
前几天到姜堰游玩,参观了泰州学派的三王宗祠故居,深有体悟,似乎找到了汪味小说的哲学渊源。泰州学派由王阳明的“心学”衍化而来,是中国思想史上唯一以地域为名称的哲学学派,其独特价值就在于开启了明清之际的人学启蒙思潮。汪先生能玩会玩,不正是自然人性论“人欲不得无”的体现吗。汪先生关注和叙写的都是底层民众的生活,都是“家常事”,泰州学派最强调的就是“百姓日用即道”,主张“百姓日用”是检验“圣人之学”的标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本身就是“道”的体现。离开了日常的物质生活,就无所谓人伦道德。从泰州学派到汪味小说,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日常伦理的重视和培育,这一思想动脉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紧要。里下河文学无法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汪味小说,但我们可以像汪曾祺那样,学学做个有趣好玩的人,玩出自己的小名堂。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