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真相》(长篇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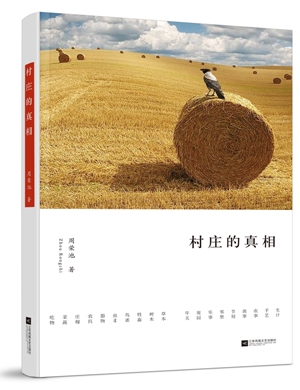
书名:《村庄的真相》(长篇散文)
作者:周荣池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书号:ISBN978-7-5399-9790-2
内容简介:
80后作家周荣池历经六年六易其稿的长篇散文作品。从物与事两个方面分十九章讲述了个人视角下的里下河村庄史,是一部安慰共同乡愁的真情之作,留住美丽乡音的现实之作,缓解城乡阵痛的唯美之作,具有强烈的缓解乡愁文学意味和记录乡村的社会学价值。
自序:
下雪了,我一直想回村庄的计划似乎又要搁浅了。
我想要回村庄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搁着。我是想回去看看那些熟悉的物事,尽管它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看来,“翻天覆地”已经不是一个什么褒义词,变化带来的所谓成就之于我对村庄的记忆而言,几乎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河流以及傍着河流生长的草木和村庄,在里下河平原乃至任何一个地方并不是罕见的事物,可悲的是他们都在以令人恐惧的速度消失在现实乃至记忆之中。所以说,回去有时候非常艰难,难以回到过去以及难以面对现实,成为今天我这个农村孩子的最大悲伤。
村庄成为废村,拆迁的那些巨额的补偿也没有能补偿人们的伤心。父亲不止一次落寞地在我们城里的家中表达了这种忧虑,他一辈子暴躁地生活在这个村落里,原先并没有看出他对村庄的热爱,及至后来我离开了村庄,他还眉飞色舞地和村里人表达了一种“鸡窝里出凤凰”的得意之情。而我写了很多赞美这个村庄的文字,即便是读给他听,他却一定也不明白——他总是会说,这个有什么好的?可是有一天,那些为了新农村发展的人盘算着拆除村落的时候,他开始焦躁不安。他不想要镇上崭新的房子,最主要的是他不能没有河流和土地,这些他怨恨了一辈子的事物,今天竟然成了令他舍不得的地方。
他没有那么矫情,更说不出怀念之类的话语,只能不安地表达着即将失去这个村庄的不安与无助。拆迁的进度由南向北,在前面的村子拆迁的时候,他曾经带着我去看那已经成为废墟的村落。我开着车带着枯瘦的老父亲走在平坦的道路上,两边的废墟让他无言以对。他不停地问我这些地方那些事情还记得吗?说实话,有些事情不会忘记,但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记忆有时候也留不住村庄里的物事,书写大多时候也软弱无力,但是我知道即便是无济于事的记忆和书写,依旧要义无反顾地进行,因为忘却就是背叛,这相比于无济于事的挣扎而言更是不可原谅的。
1
河流密布于村庄,将村庄用流水的形式网格成一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单元。村里的母亲河叫做三荡河,不知道哪个年代起源的河流,名不见经传但据说也是通到东海的。后来我读到很多和河流有关的故事,大概是百川归海的传统思想,很多传说中的河流都是通往农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东海的。我也知道村庄里的这些河名和村庄的名字“南角”一样并没有什么深意,有些河流就是当时特殊年代的形象工程,那时候每一任的村干部都以挖掘一条河流而自豪。但三荡河这条哺育了村庄的河流确实也成为一条神秘的河流,她是村庄生态的母体。
我对村庄里的河流了如指掌,尤其是三荡河边的童年岁月,让我苦涩的童年也总算有一片浓荫遍地的绿色,这是村庄给我唯一安好的印象。除此之外的苦难也并没有抹杀掉这片绿茵,只是后来“开发”这个全国人民为之疯狂,村里人也为之眉飞色舞的词,将村里的这一片绿色亲手化为乌有。
春天,芦芽齐刷刷地从黝黑的土地里钻出来。沉静无趣的土地终于爆发了她的生机。这些芦芽并不是那种诗意的芦苇,芦苇已经鲜见,或者说像我们这么贫瘠的村庄配不上那种芦花遍地的品种。但是芦竹厚实、健壮地生长着,并不要什么诗意,村里人不在意,它们自己也不愿意。夹杂其间的芦苇反而显得有些尴尬。这就像村里人都是敦实粗鄙的汉子,而那个能识文断字的秀才则成了另类一般。有一种芦苇虽然少却又格外地珍贵,即便是到今天我都没有能够明白这种叫做“钢柴”的紫色植物究竟是什么,但它在我们的记忆里是那么的高贵。植物和人的境遇一样也有一种宿命的意味,自然和社会一样也有它们静默无言的尊卑贵贱。他们都默默地遵守着这样的规则,并没有什么不安或者愤怒。所以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人一思考上帝就微笑,但是上帝不会嘲笑芦苇以及自然,因为它们都不会自以为是地思考。很多个早春清凉的日子里我在河边度过,母亲在收罗上一个冬天残留的荒草,为家里的三餐寻找点希望。我就坐在河边等她,因为我做不了什么事情,带来的书在明晃晃的阳光里也看不下去。但她满意地看着捧着书的我,她觉得我手里的书比她挑在肩上的担子要重得多。
我听得见冰冻融化的河岸边,细碎泥土散落的声音。这种声音绝对不是我的妄言与杜撰,我到今天都能记得那种破裂的细碎声响,比任何的乐音都要美妙。春天就这样在土地的松动中万物新生,直到密布的野草布满河沟,新嫩的叶子爬满枝头,母亲欣喜地擦去额头的汗水,这一年就又充满希望了。草木是守信的,他们守着冬去春来的秩序,有的甚至还守候着常绿的誓言,直到悲伤地死去。
热爱草木,因为现实中我有太多的无奈,无言的草木没有情绪,正好可以掩藏我的情绪。一个孩子的情绪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秘密,但如今看来正是那些质朴的情绪成为一个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草木有高低,如人之高矮,但似乎又不同于人的是,他们没有贵贱,无论是脚边的杂草,还是齐腰的灌木,或者是秀颀的乔木,哪怕是朽坏的枯木都一律有自己的尊严,站在村庄的角落自己的天空里与岁月周旋。一种草叫做巴根草,我曾经用来自喻,那种紧贴在地面的生长悄无声息但是生机勃勃。贫瘠的土地就像是贫困的家庭,草木和孩子们一样从来不曾抱怨过家徒四壁的日子,在四季枯荣的岁月里疯长。每年冬天,我都会到荒地里找一片荒草点燃,然后坐在有些失真的阳光里,看它们安静地燃烧。燃烧发出的声音悦耳亲切,这也是荒草们生长的一种仪式。直到土地上只留下焦黑的灰烬,我觉得经历了这个仪式之后村庄才有点冬天的样子。
灌木里有一种特别雅致的植物,就是枸杞。本来它们也是安静地生长在田边地头无人问津的。直到有一天,突然听说城里人把它当作了宝贝,村里人就在农闲的深秋,带了袋子去采那些并不饱满的果子。三荡河的两岸长满了枸杞和益母草,但大家眼里只有那些红色的果子。我们曾经尝过这些果子,那些有些草木清香的果子,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些神奇的功效。村里人在将这些野果卖给收购的小贩后,点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窃喜:城里人到底是有钱没处花。益母草也是成片地生长的,他们在河道两边的圩子上疯长,夹杂的还有气味清香的留兰香。但是这些都是无人问津的草木,尽管它们有那么优雅的名字。这些名字是我后来在读日本人冈元凤写的《毛诗品物图考》里知道的,在村庄里它们就是荒草,唯一的作用就是经霜枯黄后作为烧锅的柴草。
这些柴草比一般谷物的秸秆要“熬火”一些。“熬火”是一个很动听的词,因为这个词很实用。那种腹中空空的麦秸一着火就燃尽,是不受待见的。家里的一口锅是日子的全部,所有的事情都没有这重要。草木所有的生长都是为了日子的延续,或者说在村里人看来,他们眼睛里不会在意这些草木有任何的诗情画意可言。尽管我在后来的文字里记起三荡河边那遮天蔽日的树木,那些生机勃勃的草花,比之于烟火温暖的日子,好像并不重要了。
2
人忽略草木并不可耻,因为人还会忽略人。
捉襟见肘的日子,各扫门前雪都自顾不暇,能够在意别人有时候真的是一句空话。后来,我听很多城里人说,向往田园牧歌的生活,不喜欢城里生活的尔虞吾诈。对于这些听惯了的论调,我常常是缄默不言。我知道这些人并不真正懂得农村,他们不是村里人这个怪不了他们,就像他们经常大惊小怪地将麦子认作韭菜,而我也不曾为此埋怨过村庄里的那些不堪的日子。这些日子就是由人组成的人们过出来的,既然已经过去很久,似乎没有说的必要,可是忘记并不可能回避现实的无奈。好在我是村里人,所以我并不怕给自家揭短,更何况这些也并非完全出自人的本意,有时候是生活的无奈而已。
父亲是三荡河边的渔民,因为他嗓门大性子急的原因,那个并不怎么正直的村干部大概是为了笼络他,将三荡河边的看守树木的任务交给他,一年微薄的收入也足以缓解他烟酒告急的难处。他在三荡河边砌了小屋,在河里面支上了一架“网罾”,这种守株待兔的捕鱼方式在夏天能够大显神威。夏天对于燥热的河流而言,反而给生活添了很多的希望。他坐在岸边的树荫里午睡,酣睡的声音和蝉鸣一起,让茂密的树林越发显得闷热。父亲像是梦中能够知道鱼来了一样,会突然起身使尽浑身的力气扳下那沉重的轱辘。有时候一阵鱼入网,让他像个兴奋的孩子有些不知所措。最多的一次,要用剪刀撕破渔网,满仓的鱼虾跳跃着,让父亲经常窘迫的脸色终于舒展开来了。
丰产不丰收并不是书本上的故事,那些看似满载而归的收获也值不了几个钱。那些鱼虾兑换来的廉价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远道而来的小贩最后一锅端——大小都买走,剩下沾满鱼鳞的双手去清点那些湿漉漉的钞票。天黑了,一天又将结束,等待着的是又一个难熬的日子的到来。每天晚上,父亲都要打着手电筒去巡视那些他已经烂熟于胸的树木。三荡河边上的树木,就像是村里的邻里一样,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况他都了然于胸。但他所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它们其中的几棵会只留下一截树桩而被盗伐而去。丢树的事情并不少见,父亲也无可奈何于此,尽管他曾经恶狠狠地扬言要打断那些盗贼的腿。有一天夜里,他终于逮住了这个机会。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他和盗贼扭打在一起。那贼并不是来伐树,而是看中了村头水泵房里的电器,被父亲逮了个正着。
这件事情在村子里引起了轰动,那个平素里熟悉的家伙被警车带走,但这件事情并没有成为村里的喜事。后来那人坐了牢,父亲成为了见义勇为的积极分子去县里面领回了奖金,留给村里人议论的却只有一句话:抓贼不如放贼。父亲也并没有懊恼,只是关照我们要留心那贼出狱之后的报复。除此之外这件看似光荣的事情并没有在村庄里留下任何值得出传扬的美谈。日子把人穷怕了,人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生活,只能是自欺欺人地过着。欺负人很多时候何尝不是在欺负自己呢,聪明的人想不明白,糊涂的人可以不用去想。独居的“呆老牛”,沉默寡言地生活在水边暗湿的小屋里。他没有田地,村庄就是他劳作的田地,犄角旮旯里被他寻摸遍了,所有的垃圾在他笨拙的眼睛里都是宝贝。他的工作有个不错的名字叫做“拾荒”,倒也没有把他说得那么悲惨。但这些绝不是显得村庄对他有任何的善意。
有一天夜里,他在屋里哭闹起来,他的哭叫声真像一头悲伤的牛。许多人带着不同的情绪不顾困意来看这一出好戏。据说他有不少的积蓄,可就在这一夜里被洗劫一空,那些藏在被胎里沾满灰土的钞票被偷了,连同那带着臊臭味的被胎也被一把火烧了。大家唏嘘不已,但并没有人去劝解他,似乎这种人不需要安慰。大家的精力都用来揣摩这个盗贼是谁,直到毫无结果怏怏而去。后来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出了是他同宗的侄子偷了钱,但是这个侄子指着天发誓说没有,说就是一场火烧没有了。后来这个侄子很早就死了,死在了呆老牛的前面,这成为这个无解案件的一个安慰。苦难就像是呆老牛身上的油污,一年四季天长日久不曾被抛弃。于是,日子的龌龊与肮脏就这样被顺理成章地接受,以至于慢慢地变成生活的一种乐趣,给那些有些麻木的谈论者以最为重要的谈资。
谁也不知道,在那些安静的黑夜,以及在那些阳光明媚的白天,穷得只剩下叹息的日子里上演着不堪的情景剧。我后来把这些故事讲给别人听,讲的时候我自己都不再相信了,我也没有指望别人会去相信这些,但事实是你忘不了那些似乎早已经远去的故事。那个叫做黑皮的男人大概已经死去了,至少我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他跑到那个懦弱男人的家里,睡了别人的女人,让他的男人在村子里成了悲剧。但是他并不怕纸包不住火的丑态,戏剧性的是以后两个男人和女人一起相处安好地睡在了一起,于是悲剧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喜剧。
如果说村庄还有一点点温情,不会是在倒春寒的日子,不会是忙碌的秋收,也不是冰天雪地的冬天,而是那些蚊虫满天的夏天。人们终于没有办法再躲在自家的屋子里盘算着自己的日子,而是被暑气逼迫出来,在布满星辰的夜色里和气温抵抗。那些乘凉的夜晚,成了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为了驱除身体的燥热,大家争相讲述着已经讲了多少遍的笑话,那些笑话其实很残酷,依旧是生活里的悲剧,但是被在黑暗里无数次讲解和演绎,终于还是从悲剧变成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喜剧。多少年后,我想想起这些有趣的故事,才明白“苦中作乐”这个词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村庄里人的出生似乎都是悲剧,戏剧性的是人把这样的日子过成了喜剧。就像我自己的出生也似乎是一出悲剧,母亲在临产前走失,生下我后又因病糊涂地离家而去。我便在父亲满是酒味的气息里开始了自己的一生。我曾经喝过一个痴呆母亲的奶,这个女人我见过,她的女儿也总是痴呆地站在村头流鼻涕。那个女人的身上总满是油污,就连那绿色的头巾也裹不住她头发上的油腻。她的丈夫是一个和尚,是一个被生活逼得无奈去学唢呐念经文的和尚。他念经回来买了红色包装纸的火腿放在家里,告诉自己的婆娘那是蜡烛不能吃。这是一个村里流传很久的笑话,但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我觉得这个痴呆的女人也不好笑,说到底我是不想嘲笑自己。
3
尽管如此,日子还是有自己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的就是节刻与风俗,冷暖变化只是日子的外形,支撑日子循环与进展的就是那些固定不变的节日与风俗。从春节开始,从春节结束,这个传统的日子在里下河的村庄里也照样是隆重的。穷困并没有抹杀掉人们过好日子的愿望,于是即便再困顿与窘迫,节日和风俗都是日子里坚守不变的信条。关于这种信仰,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时候他兄弟姊妹多,日子自然也捉襟见肘,但是年节总是马虎不得,于是人家的孩子有花戴,没钱的就扯上二尺红头绳——作为一个团圆的日子,汤圆是不可少的口彩,于是便将苦涩的慈菇削去了尾巴,煮熟了成为一个个的汤圆。
多少年后,当汪曾祺先生的咸菜慈菇汤和慈菇烧肉成为名菜,那些苦涩的慈菇成为趋之如骛的比土豆“格高”的名牌之后,在一个个贫困的家庭里只能是一种无从选择的面对。但总算是把苦日子过成了好日子,因为有坚持不变的那些信仰。节日和风俗作为村庄的信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悲与喜本来就是日子的常态,生与死就是日子的来去,这一点并没有什么深奥值得去挖掘。倒是那些细节如今看来算是有些令人动容的,同样是因为把苦涩硬是过出了甜味。
所有的节日里有关生死的最为庄重,不是因为生的喜悦,而是因为死亡的恐惧。清明、七月半、立冬以及祀年将生死在日常与过往连接起来,说到底害怕的是不可琢磨的明天。“早清明,晚大冬,七月半的亡人等不到中”,这些颇有些庄重的日子,人们终于因为死亡而屈下顽固的膝盖,在亡人的灵位前祷祝着余生的平安。一年春和景明的清明,我坐着父亲的船从三荡河出发去一个叫做三荡口的地方祭祖。三荡口并不是三荡河的源头,但是从这里一个草木凄然的孤岛上分流出到各个村落的支流,就像是族谱上那一根根维系着血脉传承的红线,串联着枝枝蔓蔓的子孙后代。
那一年的春天真是明媚,清凉的河水里沉睡的河草被父亲手里的竹篙搅醒。两岸的草木也都醒来,张望着暖融融的阳光。那些瘦弱的小蛇从水上游弋而过,它们似乎也要去寻找自己远去的祖先,在清净的河水里留下瞬间消失的痕迹。祖坟之上并没有什么显赫之处,草木的生长让日子有些荒凉,那些沉默无言的坟冢早就忘记了人间的悲哀与喜悦。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挖开了沉睡多年的祖坟,因为要开发河荡的缘故,他们要把祖先请到另外的地方安息。当泥土被翻开,没有什么故事的坟头还是被挖掘出神秘与忧伤。那些已经朽坏不堪的碎骨在明媚的阳光下已经失去了死亡的恐惧,就像是一次普通的搬家一样,在炮竹声声中父辈们完成了这一次迁坟的仪式。
从此之后,我虽然很少再去这个被父辈们看得很重的地方,但是那一抔土中的记忆从来没有被忘记。父亲曾经过继到三荡口的村庄里生活过一段时间,老人去世之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带回来的东西有三样,一对木门,一只茅缸,还有一副对联:爱莲世泽,庆远家声。这副对联就是一个姓氏的家风,也是不可丢弃的信仰。
生死自然不会被忘记,因为人就是在做生死这件庄重而又无奈的事情。因为母亲的早逝,我对于事关生死的仪式经历得记忆深刻。本来以为卧床多年的母亲离开这个世界除了悲伤之外是她的一次解脱,然而她离开之后的种种仪式和风俗让我对贫困的村庄和困难的日子又多了一层敬重。离开原来并不是那般的轻而易举,甚至比活着更加繁缛,将悲伤变得更加的沉重。
我曾经为此不以为然,大概是因为读了几本书的原因,更觉得简单会让离开少些悲凉。母亲出殡那天,依例要进行一种叫做的“抬轿子”的仪式。纸扎的轿子抬出去,由儿子抬着,亲人们一队人沿着村庄绕一圈择地去焚化,这是有点彰显孝德和家门威风意味的。母亲的娘家人提出来要儿子赤脚,这在寒冷的冬天无疑是一种苛求。但是娘舅的儿子们并不愿意让步,百般协商之下同意起码赤脚穿上草鞋去走这一段路,理由很简单这才能记得住娘恩。娘舅的权威不可挑战,否则到死者七七期尽要“烧房子”的时候,娘家人不点火,这纸扎的房子就成不了娘亲的阴宅。宁死做官的爹,不死讨饭的娘。离开的悲伤被那些仪式变得更加的沉重。也正是这些风俗和仪式的重量,让苦难的日子能够顽强地过活起来,似乎是这些仪式支撑着生存和生活的信仰。
同样,执守着村庄的这些信仰和秩序的还有那些器物,那些静默无言但却不可或缺的器物。它们同样是村庄的主人,因为它们和村里人一样执守着村庄的信仰,它们甚至自己也成为村庄秩序和信仰的建立者。无言让他们在沉默里孕育着一种特别的能量,端坐在某一个角落,像是字画上的一枚印章一样成为重要的确认。一个家徒四壁的家里,人们所看重的也许不是锅碗或者床铺的设置,反而会是有些不可琢磨的“家堂”。堂屋的正中端放着的案几,香炉烛台以及敬奉着的红纸写就的“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成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信仰。菩萨吃不饱哪里有凡人的饭吃,香炉里的香灰满满地堆积着,就是信仰的充盈。这样,一个家,一个村庄才能站得住脚跟。
还有那些笨拙的器物,那些已经修补过的船只,那些朽坏的农具,虽然没有什么珍贵可言,可是他们和父辈们一起守候着土地与村庄,成为村庄不可缺少的角色,组成关于村庄记忆的一串串关键词语。
4
冬天,村庄被慢慢地冷却下来。
生长开始缓慢,生活开始减速,生计开始艰难。刚刚经历秋季的“收获”这个词对于一年的辛苦来说,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值得庆祝一番的事情。可当肩挑背扛地将谷物从田亩之中收获回来,心里早就开始盘算着这一堆粮食的分配。上缴的、还债的、孩子的学费以及家人的药钱之外,留作口粮的堆进粮仓叹一口气却轻松不起来。庄稼是日子里的大事,正是因为这件大事总是解决不好,日子总是捉襟见肘。也许是黝黑的水稻土太有黏性,总是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无法逃离。没有土地就没有日子过了。这是村庄里千年不变的信条,却在一天黎明被改变。
那个寒冷的黎明,父亲最小的弟弟在窗户口喊了一声:大哥,我们出去打工了。对于他的这个决定长辈们也不无担忧,但是这个身强体壮的“老巴子”还是登上了远去的客车。他要去的地方我们有人听说过,还有人没有听说过,村里人就连进一趟县城都是远行。奶奶曾经埋怨说那里有金山银山我们不要,可是这个倔强的老巴子也坚定了不要守在村里的想法。他有一身的好手艺,十多岁就因为不愿意种田,跪在师傅门前求他学艺,不几年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好瓦刀”。他砌墙造屋的技术一流,尤其是“支锅”的技术好,支锅是有些技术含量的活计,锅支得好省柴火还热得快。他看起来孔武有力,但是手上功夫很灵巧,锅灶砌得很精致,特别是墙砌好之后,用草灰和石灰搅拌成涂料涂在墙面,然后画上两条活蹦乱跳鲤鱼的场景令人赞叹。鲤鱼是祥瑞的动物,年年有余画在锅灶之上是一种美好的向往。灶台上还设灶君的神位,贴着灶王爷的神像,旁边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村里人总是因地制宜地表达着自己的向往。
手艺是种地之外混饭吃的营生,也像是一种有趣的仪式,尽管这些手艺被农人们所不齿。其实这些认为是“奇淫技巧”活计的看法多少是有些眼红的意思。靠力气吃饭的人讲得是蛮力和踏实,他们见不得那些手掌之间的把戏,但生活恰恰又离不开这些把戏。手艺人的手艺将贫困的日子增添了许多的乐趣。木匠将看似不成材的树木变为精致的家具,铁匠将废铜烂铁变成精巧的器物,篾匠将江西运来的毛竹编织成灵巧的物件,焗碗的在破裂的陶瓷上留下精心的印记——这些原来是农闲之余的营生慢慢地变成了经营。当农本被这些慢慢取代的时候,农人的恐惧逐渐变为一种怡然自得,蛮力被巧劲取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起来。
于是离开与出走成为村庄所面临的必然选择,成为老人对下一代的既爱又痛的面对。村里的年轻人离开村庄大概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求学,一个是读书。虽然村子里只有一所几十个师生的村小,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是连我那一字不识的父亲也是懂得的,因此由于求学的离开是一种荣耀,备受人们的羡慕。而“打工”这个词比求学辛苦得多,况且只凭着手脚进城,对于有脑子的城里人来说,乡下人的自卑感总是和破旧的衣服一样,想甩也是甩不掉的。但打工者并没有输给求学的,他们凭着自己的气力成为城市的新阶层,并且以几何级的数字增长,为“劳动密集型”这一个资本神话奉献着自己的气力甚至是生命。
他们不仅改变了城市,也在改变着农村。三荡河边的茂密树林终于命运不保,那个隐藏了一个少年十多年梦境的桃花源终于要面对“开发”这个看起来热气腾腾其实是杀气腾腾的词汇。当挖掘机第一次出现在村庄的时候,那个满身酒气说着北方侉话的工头并没有受到里下河土地和村民们的礼遇。他们的机器被人用石子堵上了排气口,急得在黝黑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方言骂别人的娘。可是村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不能不种粮食”的话并不是捍卫土地,而是在土地流转金的问题解决之后,爽快地按上了粗糙的手印。
所有的树木被砍伐一光,所有的路上被厚实的混凝土覆盖,所有的河流漂满富营养化的绿苔,所有的良田成为高效养殖示范区牌子下的聚宝盆。耕田的双手成为数钱的能手,走路的双脚变为踩油门的司机,瘦瘦的脖子上竟然也扎上了并不平整的领带——这其中就有我那个当年外出打工已经致富,却又返乡养殖成了能手的小叔叔。我外出求学十多年后回到村庄,一脚踩上水泥路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一丝的踏实。除了日渐破旧的屋舍和慢慢老去的父辈,村庄已经慢慢地和外出的孩子一样,离开了我的记忆。
留在农村里的还有老人和猫狗,就连那些鸟雀似乎也并不那么守时地来去,变得日渐稀少。猫狗巡行在村庄里,它们也是祖祖辈辈不曾离开的居民。他们在土地上奔走,叫春、交媾、生育、老死都不曾离开村庄。我曾经在村庄不远处的一处古村落遗址里见过一只狗的化石。似乎还能听到七千年前它死去时候的哀嚎。它并不是死于病痛,而是成为祭品。那时候聚落在里下河的祖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仪式,为建造聚居的村落,他们用狗作为埋在房屋础柱下的祭祀品,祈祷房屋和村庄的安宁。几千年后祖先的村庄重见天日的时候,水边林间火热的生活似乎还依稀可见。男人们举起长矛射向猎物,在沾满血迹的猎物身上撒上茅草跪拜庆祝,女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并不饱满的稻谷收集起来存放在粗糙的陶罐里……刀耕火种的农耕生活养活了几千年饥肠辘辘的日子,最终还是成为博物馆里聚光灯下的遗迹。
而我们在将祖先生活的村庄挖掘出土安顿为一处著名的遗址时,竟然也在亲手将自己的村庄变为遗迹。不是因为风霜雨雪的灾难,而是用现代化的工具毫不心疼地将村庄拆卸一空。这比灾难更为令人痛彻心扉,更为心痛的是我们在为这些灾难洋洋得意,毫无愧悔之心。作为一个已经离开的孩子,我再也没有在村庄里住过一个晚上,那些曾经充满故事和神秘的夜晚,也留不住我的脚步,我不是不想留下而是早就心知肚明地理解,我根本就留不下来了。
虽然家还在,可村庄已经废弃,家园已然丢失。而我希望在纸本里寻找的不是故乡,是一种对家园丢失城乡对抗的缓解,因为我们已然不想回去,事实也回不去,但是至少我们又是不可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