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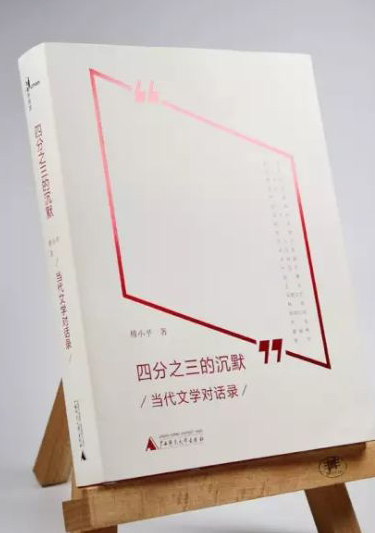
书名:《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
作者:傅小平
书号:ISBN 978-7-5495-8092-7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定价:58元
自 序
我在年少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里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一部写不完的长篇小说。我至今没能忘却这个梦,隐隐觉得,在内心深处,许是对写小说的不可救药的执念,还有为迟迟没能写出感到的亏欠,才使我像是循着某种命定的轨迹,不改初衷走在对话访谈的路上,直到有了眼前的这本对话录。不过也好,如是应了杨炼先生“傅小平的文学对话,本身就是精彩的文学作品”的誉美之辞,这部汇合了二十一位小说家、散文作家、诗人对话的集子,依然可视为我期待中的,对于写作执念的“拥抱之书”。
一
这本书的“第一页”是由张贤亮写下的,虽然没有把这篇对话放在第一页,对他的采访实际上也只是我十年记者生涯里的第N次。我这么说,是因为张贤亮不只是打破了我对一般作家的固有印象,还洞开了我近乎第六感的某种感觉。他告诉我,一个作家原来可以这么说话,可以这样不走套路,你的思想和言说也可以不为任何东西拘囿,而是像不羁的灵魂一样自由。我至今仍能清晰触摸到采访他之前的紧张忐忑,还有采访结束后那种不可言喻的痛快和释然。
不久后,张贤亮来到上海,编辑部在外滩附近一个停有海盗船模型的酒屋里宴请了他,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听他漫无边际地神聊。印象中,他什么都谈,他谈到了我有所耳闻的一切,也谈到了我闻所未闻的一切,他没有如我们所想谈文学,谈小说。当时真想问问他,为什么不谈,却终究是没问。我想要我问了,他或许会反问我,为什么要谈?你说说,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而在他的反问里,其实已经包含了回答:文学就是一切,文学可以是文学之外的任何东西。
现在想来,张贤亮的不谈文学,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热爱文学。在大起大落的人生里,张贤亮变换了很多角色,他的文字风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写作的挚爱。我曾问他为什么写作?他说就是好玩。我当时并不怎么理解,只有等到两年前张贤亮去世,《新民晚报》记者让我回忆与他接触的印象时才豁然醒悟到,他说的好玩并不是玩世,而是一个人真正回到内心之后的真诚与纯粹,而好玩的背后,依然是深切而真挚的关怀。一如他的大俗,真正指向的是他的大雅,而在大俗的外衣下包含的是深刻的内涵。又如他的随性,其实不是随意,而更多是为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敢于慨然自言“最有争议的作家”的,那种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此刻,我又想起他在他兄弟的陪同下,沿着福州路熙熙攘攘的人行道渐行渐远,最后在拐角处消失的身影。在他离世后,我唯一能期望的是,如他这般的格调和境界,并没有在我们这个世上随风而逝。
二
翻开“下一页”,读到的是莫言。在这本对话录里,与莫言的对话,确是我继张贤亮之后做的“下一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只要是跟他扯得上边的书,都不能不提他。我的不能不提,却不是因为他是莫言,而是因为他甚是可言。对他的采访告诉我,只要你保有真诚和善意,作家是听得见批评的,而且是可以锐利批评的。其实,刚进报社不久,我就听编辑部同事做过一场“现场直播”,是我们一位记者在前方“阵地”第一时间发来的讯息,她目睹了莫言和一位知名评论家的交锋,最后这位前同事下了一个结论,你的一轱辘批评,也架不住莫言如黄河之水般奔腾不息的滔滔雄辩。你甭说当面批评莫言了,还是等着被他批评吧。想来是不经世事的懵懂,那时也没有多想,我所想的只是,既然读《蛙》读出了那么些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当着他的面问问他呢?话虽如此,在赶去采访时,心里还是直打鼓。现在想,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惟愿当时是准点到的他入住的房间,因为怕迟到,偏偏提前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我不得不来来回回在走廊里走着,等待的时间是如此漫长,眼前的路像是永远没个尽头。
说来这是跟莫言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采访结束的几年里,我也在其他场合远远地见过他几次,不管他是一个人待着,还是被热心的读者簇拥着,我都没有上前请教。后来因为一些事找过他,他也帮忙,给他去过几次信,他都一一回复。这次出书,因为要找照片,翻出跟他的合影,依稀觉得当时采访的感觉又回来了。在照片里,我站在一旁,莫言是坐着的,他大抵享受坐在低处的感觉,他是从内心里把自己放得很低,而正是坐在“低处”,他构建起了站在高处的叙事奇观。
不能不说,就我接触的感觉,莫言从里到外都透着为国内文坛少见的大家风范。这部分源于他的天性,同时也是修炼使然。我记得我抛给他那么多会让一般作家感觉难堪的问题,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大度地说,要是出书前给我看看,就能避免一些问题了。这是他的谦辞,但在他说的时候,却分明能让你感觉到他的真诚。不确定当时是不是被深深感染了,等走到大堂,我才想起把围巾落在了他的房间里,只好问他拿了钥匙回去拿,等我赶回大堂,他和他的责编依然等在那里。再后来,他第二天从上海回到北京,我自觉批评得过分,心有不安地给他发了短信表达歉意,他很快就回了。他说,他刚进家门,我批评得在理,我认真读了他的书。我似乎能听到他开门进去,又把门关上的声音,从遥远的时空传来。
三
事实上,一次次采访就是在出门、进门与关门的角色转换间完成的。出门前做好功课,可让自己心安踏实,亦是对他人的尊重;进门后,从开始的磕磕碰碰,到渐入佳境,最后让真实的声音自然流淌;幕布放下,出得门来,若是心有所悟自然是好,如果觉得没什么,亦可放下安然。我也听人说过,一个好记者便是,即使别人把你从大门赶出去,你也得找到窗户爬进来。我不曾有这样的经验,而即便是门上有窗,且窗是开着的,我也会抵制爬进去的诱惑,而是尽力说服别人把大门打开,让我站直了像个人样地走进去。当然会有说服不了,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那就悄悄地走开,等下次机缘巧合进去,或是永不回返。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娱乐至死的当下,我自认不是一个好记者,我缺乏这个职业必需的与人周旋的那份耐力。在一些场合,我羞于前去和人攀谈,而很多时候,我也更愿意坐在无人打扰的角落里当听众,听到会心处,任凭心里波澜起伏,要没什么可听的,亦不必装作在听。我也没有听从前辈的忠告,去和作家交朋友,私心里,倒是觉得保持距离为好。既然所有的碰撞、交融,都是在两个人的坦然面对中完成,又何必在意完成后会怎样呢。要以后遇见,远远地点个头,或像不曾认识似的擦身而过就挺好。重要的是,在我感觉里,彼此珍重那份“门里见”的真诚与美好。
当然,并非所有的采访都是美好的,或说正因为恰如其分的美好的不可多得,更让我觉得弥足珍贵。无论是贾平凹“这是我最长的笔答。这是因为您问得有水平,让我兴趣”的认可,还是苏童“你的这些采访问题真是折磨到我了,好在咬咬牙也坚持答完了,花了我三个半天”的较劲;无论是毛尖“说真的,打开你的问题,吓了我一跳,知道自己碰上不好对付的了”的调侃和“感谢你的问题和耐心,印象深刻”的评语,还是安妮宝贝(庆山)“问题里可感受到善意,认真,理解和敬业”的回馈,都会让我感受到以心换心的美好。如果说,精彩的回答往往是由精彩的提问唤起的,精彩的提问也常常是由精彩的回答推动的,而在这一问一答中,我也的确感受到了美好的情谊。比如高尔泰先生,如果非要我选一本汉语文学的枕边书,我会选择他的《寻找家园》。我真心希望不只是国内,也不只是华语世界,都能有更多的读者读到完整版本,但这本书译介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让人唏嘘。因为看到译文有调整和删节,他不能接受在国内炙手可热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译本问世,以致一向为中国作家围着转的葛浩文听闻惊讶不已。但如高尔泰所言,“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就是阉割”,他理应拒绝这个不真实的译本,“不仅是拒绝一个大牌的傲慢,更重要的是:我拒绝一种对于其他民族苦难的冷漠。”他的拒绝,使得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徒然生出许多波折,此中经历均一一记录在收入他繁体字版近著《草色连云》的《文盲的悲哀》一文里,字里行间透出的那份绝世的纯粹和高贵让人动容。但他并没有因为在高处而少了谦和。有了第一次的采访后,我推门进去,却不见了门,我可以和他做没有门槛的舒心的交流,当然,那很多已是另一种心灵对话了。
四
是的,对话,我把这本书命名为“对话录”,是因为你看到的并非习见的,充满了成功者的人生传奇、励志故事、闲趣八卦和观点记录的访谈,是因为相比访谈的过程,我更为珍重对话的呈现。或者说,我从内心里倾向于如长江三峡般遍布峰谷与险滩的,“难以对付”的对话,而不能接受不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很可能包含了曲意迎合的意图的,过于平滑的访谈。我们确乎是太习惯于假装没正经的八卦、吐槽和闲聊,太习惯于一本正经的演绎、推断和论定,而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真实的思考了。禅宗有言,祖师对初学者常不问情由,当头给以一棒,以考验领悟佛理的程度。如此,于情于理都不是我能做到的,反倒是我更需要高人的棒喝,以促我警醒。但如是把棒喝作截断解,禅宗的这种态度,却是我们都可以借鉴的。在对话里,我想说的是,去你的平静吧,我们需要的是摇晃,不安的摇晃,让思想的激流一遍遍冲刷意识的堤坝,直至它摇摇欲坠,轰然决口。我也会不时打断对话者一个人的“独白”,让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声音参与进来,让这些声音与声音碰撞,形成复调、变奏与交响。我知道这会让本可以稀松平常的访谈变得异常紧张。但我相信这紧张里,隐藏着思想的本质,而它总会在紧张到死的最后一刻呈现。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记下这些对峙、矛盾、驳难,因此也更显五彩斑斓的声音,也试着以此开启一个有着更多真实,更多可能的世界。
这本书命名为“对话录”也因为,对话能让我保持基本的诚实。经常被朋友问到,为什么不写写批评文章呢?这问话里的意思是,这些对话中有一些提问,把它独立出来再做些补充和阐释,就可以写成一篇篇独白式的批评文章了。这样省力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我一般会找理由说,我想表达的,在提问里都表达了,再展开就重复了。但往深处想,很可能是我的审美感觉,正如苏珊·桑塔格在一本书里写道,她所写的——还有她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艰难地从错综复杂的状态的感觉中获得。而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又有如网一般相互联结的多个面向。如果说,面对一个文本,就是面对一个完整的世界,只是从一个或几个面向切入,就会牺牲这种感受的全息图景,这会背离我面对一个文本时生成的原初的真实感受,对话却能让这些感受最大程度留存。而换个角度看,我服膺尼采说的,最最深刻、最最丰富的书籍总是拥有一些类似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具有格言特点的突如其来的思想。由是,在他自己所有的书中,所有的章节里,都只是一个个段落的集锦。米兰·昆德拉说,那是尼采为了让一个思想由一口气息说出;那是为了照着它当初迅速地连蹦带跳地来到哲学家脑中的那个样子把它固定于白纸黑字。而这一个个段落也未必是没有抵牾的,我要做的是让这些随话语的机锋不断变换着面貌的对话成为矛盾的统一。这正应了桑塔格在谈到自己运思的过程时说的,这个,对。但那个也对。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更像是转动一个多棱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某件事。而让一个个文本透过多棱镜,在当代文学的长廊里留下丰富斑斓的光影,这是诚实的对话有可能做到的。
我的珍视对话,还因为这合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美好意愿。要我说,对话如果说有什么重要性,就是它提供了我们弹性碰撞、自由争论和激发思考的空间。以我的理解,我们渴望栖居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对话性的,由对话才会走向真正的包容与理解,而文学因其天然的民主性、多元性、开放性,为自由平等的对话提供了最好的场域。文学的创造重要若此,正如乔治·斯坦纳感叹,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但敲打依然是值得的,与创造媲美的会心的敲打更是可贵的。就像是《神曲》里于人生中途迷路的但丁,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灵魂,引领着穿过地狱、炼狱,得以遇见情人贝阿特丽切的灵魂,共享游历天堂的荣光。对话者正是那个引路人,在你的追索和敲打下,领着你奋力向上,要最后有幸得到文学女神的青睐,恰可以一道探究文学创造的秘密和福祉。这并不是说对话者掌握着最终的阐释权,有时甚至他会迷惑于在对话中对自己的创造竟有如许的发现,但如是以阐释某种意义上即对话论,一种被批评或言说的对象同时在场,而非被缺席表扬或审判的批评或言说,却无疑是值得珍视的。在对话里,你能看到对话者,亦即那个引路人的在场,并真切地感觉到对话双方一种充满可能性与创造性的张力,这在当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五
既是对话,何以取名《四分之三的沉默》?说来这只是我和妻子谈到这本书时,她在直觉的瞬息捕捉到的意象,却未尝不是道出了某种深层的意味。
对话的反面不就是沉默?如鲁迅在《野草·题辞》里所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我们这个聒噪的小时代里,我们说了太多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沉默了,又或者我们早已忘却了沉默,忘却了维特根斯坦“对于那些不可言说的,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的告诫,以致对于不可言说的,我们说了太多;对于需要言说的,却是说得太少?我们确乎是太有理由不安于沉默了,在这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年代里,完全的沉默,无异于湮没。那不如让沉默,成为这四分之三的沉默吧。比之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有海面以下四分之三的“沉默”,才会有海面之上四分之一的真实的“言说”。而这沉默的部分,并不是失语,而是自觉到虚假浮泛并起而反抗时,迸发如闪电的沉默的言说。
这是有良知的对话可能做到的。我读到有媒体人,在为一本访谈录所做的《跋》里说,某主持人在做一档文化节目时,基本上,每个嘉宾的前两个小时谈话,都会被直接删去。因为再有经验的被访者,聊到两个小时后,提前准备的废话也会被耗尽,之后,才有可能出真东西。我不曾有过这样的奢侈,我担心聊到疲惫后说出来的话会更显苍白,正如我担心仿佛是在不可期的瞬息中,领受了狄兰·托马斯的启示似的,那种“催动泉水挤过岩缝的力”,会在岩缝洞开的流淌中枯竭。也因为此,我们更需要直追本源、直指人心的对话。
六
对话需要听见,而沉默更需要听见。事实上,这本书最开始的书名即为《听见》。在写了又废弃不用的一段文字里,我写道:倘是缺乏被经验到的更为开阔的视野,缺乏被反思过的坚实的价值坐标,再多的所见,也只会在你的眼皮底下溜走不留一丝踪迹。也因为此,我们需要听见。我也确信我听见了什么,而我的听见,部分也是因为把一些想见的、看见的,转化成了听见的,就好比是,从稍纵即逝的一闪念里“听见”遥远的回响,从树枝的轻微颤动里“听见”风的声音。
而我的渴望听见,也是因为世界需要“听见”。因为很多的“听而不见”,世界陷入无边的荒芜与孤寂;因为很多的“听而误见”,最初的谬误,会被无数级放大,终成了无关真相的谣言和谎言;因为很多的“听而浅见”,生活的复杂性,于被无限简化和抽空的结论里变得空空荡荡;因为很多的“听而娱见”,一切都被戏说,而我们也终将在这日甚一日的娱乐的掩盖下,所见只是一片苍茫茫的虚无;因为很多的“听见”当没“听见”,那些应当被尊奉的价值和原则隐匿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我们的苟且,以及在我们的苟且中失落了尊严的世界。
如此,似乎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我试图“听见”,却是因为很多的听不见,而如果说我“听见”了什么,正是因为我始终心存对听不见什么的疑虑。我听见的,并不常是那些诗意的景象:群山回响、万籁俱寂、风吹日落,抑或是静水流深。我听见的,常是枯枝在劲风里的撕裂,浪花撞碎在冰山上的钝响。这种种如同暴雨将至的震惊的体验,也注定了我的很多“听见”,并不是印证了自己所想、所愿的“听见”。往往最初的期望,总会变成诘问。我所做的只是悬置决绝的判断,让确信变成怀疑,让结论变为前提,让很多看似完成的事物,在行将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
于是有了这本近年部分对话的结集。我不曾追随前辈职业记者的风范,面对要采访的人物,放好录音笔,摊开笔记本,然后做轻松状:说吧,让我们从头说起。我渴望的是那种紧张,与真正的创造相媲美的那份扣人心弦的紧张。我会充满歉意地说:说吧,从中间说起。让我们把所有的成见统统抛开,在枝叶披拂、藤蔓交缠的丛林里,走出一条无人走过的林中路来。
我也无意于以我并不纯熟的抒情笔触,记下每个对话者的笑声泪影。这自然是因为对于每个对话者,在我之前已有很多的印象记录。在我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印象记录,而每一个对话者的荣誉,归根结底只是围绕他的名字聚集起来的或有几分精确,更多是误读的印象记录的叠加和呈现。我不想,也无需再为这些对话者的荣誉添加注解。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这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不可复制的形象,一定是隐藏在他们的声音里,正如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创造者而言,他最自然的性情,一定是体现在作品里,而不是在作品之外的任何地方。
七
一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小结,也是一次重新出发。我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所以我们奋发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去,直至回到往昔岁月。”我知道我们的向后推去,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包含了现在和未来维度的一次次回溯。
因为真正的“沉默”,真正的“听见”,在世界深处,在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