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编说
从1978年到2018年,《钟山》杂志走过四十年的岁月。一路走来,《钟山》秉持“兼容并蓄、惟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的办刊宗旨,始终以不卑不亢的姿态、高屋建瓴的眼光、大气厚重的品格,深度介入了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值此创刊四十周年之际,钟山君特推出“回眸四十年”栏目,与诸位一同翻阅老杂志,回望那些依旧在长河中发光的文章,重温《钟山》这一壶历久弥香的佳酿。
自创刊以来,《钟山》旨在“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而作为具体策略就是要“引领潮流“,通过对文坛生态的主动应对姿态来引领文学思潮。上个世纪80年代末,《钟山》对“新写实小说”的命名和倡导,就充分体现了其办刊思路的策略性和文学思维的先锋性。
本期微信,跟随小编回到历史现场,共同回顾“新写实”思潮的始末,钩沉往事,以期新知。
潮起
上世纪80年代末,文学创作出现新动向。一方面,“寻根文学”己难以为继,先锋小说的艺术探索难以在更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整个文学已出现一种疲软状态。另一方面,当时新冒出的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如《伏羲伏羲》《塔铺》《新兵连》《风景》《烦恼人生》《天桥》《厚土》《枣树的故事》等小说以新的精神和新的技法,昭示着某种新小说的潮流即将到来。《钟山》编辑们敏锐洞悉当时的这一文坛态势和创作趋势,萌生出为这些新小说创办一个新栏目的设想。1988年7月17日,当时的编辑徐兆淮和范小天赴京拜访作家、评论家、报刊编辑等30余人,代表编辑部说明创办这一专栏的背景、设想及围绕这一专栏拟举办的评奖、出书活动。大部分作家、评论家深表赞同,并愿意积极参加活动。1988年10月中旬,《钟山》与《文学评论》在江苏无锡联合召开“现实主义文学与先锋派文学”讨论会,以初步试探文学界的反应。 陈骏涛、陈思和、南帆、吴亮、丁帆、王干等学者和评论家在围绕现实主义和先锋派问题展开讨论的同时, 不约而同地对这股写实潮流进行了讨论,有称其为“新写实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 ,还有的则命名为“后现实主义”。在此之前,《钟山》执行主编徐兆淮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说法,并与丁帆在《上海文论》上以专文论述“新现实主义”。会议上,《钟山》编辑王干“试图用‘后现实主义’来概括刘恒、刘震云等类似作家的创作”,但遭到了与会者的不同意见,并在许子东“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悠然提议中结束话题。另外,由于“讨论会上,‘现实主义’一时几乎成为一个忌口的词”,而“新写实”的提法倒是收获了一些温和的反馈。
定音
经过前期理论酝酿,《钟山》1988年第6期刊发文讯,预告将于次年初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这是“新写实小说”的说法在文坛第一次正式出现。“新写实小说”这一名称也就随着《钟山》的“大联展”被一锤定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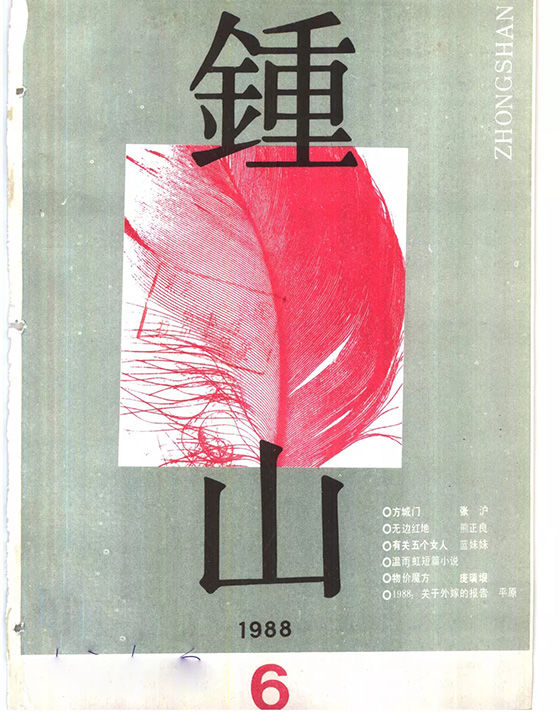

(《钟山》1988年第6期 )
1989年第3期,《钟山》新栏目“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正式出炉。《钟山》在当期卷首语中界定了“新写实”的概念、特点、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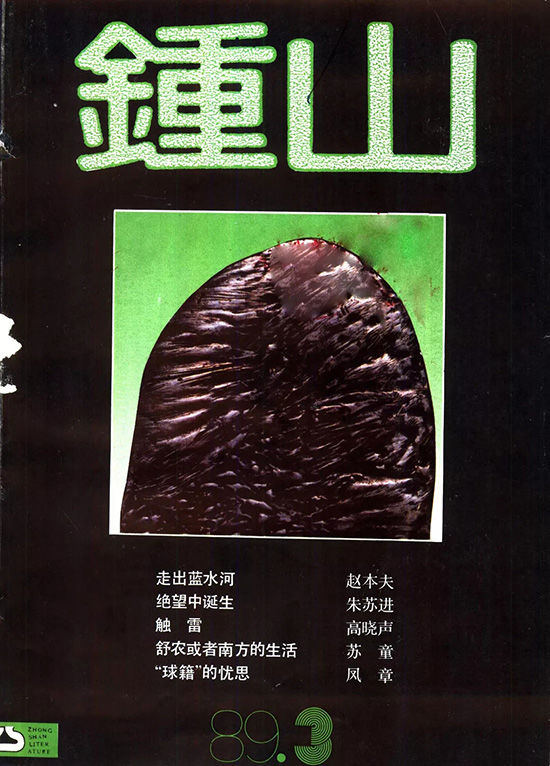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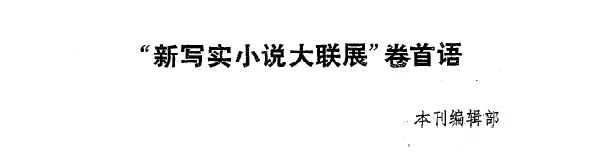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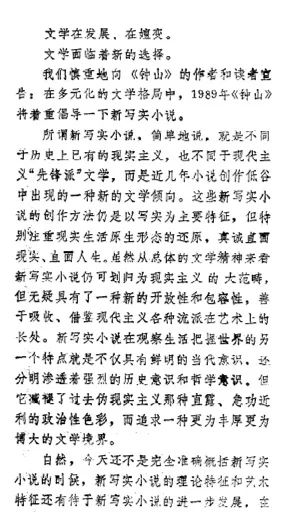
(《钟山》1989年第3期 )
实绩
从1989年第3期至1991年第3期,“联展”活动历时两年多,一共举办了8期,共推出23位作家的26篇小说作品,具体情况如下:
1989年第3期
《在绝望中诞生》(中篇)/朱苏进
《走出蓝水河》(中篇)/赵本夫
《造屋运动及其他》(中篇)/姜滇
《触雷》(短篇)/高晓声
1989年第4期
《千万别把我当人》(长篇)/王朔
《顾氏传人》(中篇)/范小青
《灾年》(中篇)/蔡测海
1989年第5期
《逍遥颂》(长篇)/刘恒
1990年第1期
《龙年:一九九八》(长篇)/梁晓声
《供春变色壶》(中篇)/程乃珊
《六十年旷野》(中篇)/张廷竹
1990年第3期
《日祭》(周梅森)
《钟声》(史铁生)
《渐入胜境》(唐炳良)
《雨季之瓮》(吕新)
1991年第1期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刘震云
《采红菱》(中篇)/叶兆言
《陈焕生战术》(短篇)/高晓声
《狂奔》(短篇)/苏童
1991年第2期
《爱情故事》(中篇)/林谦
《鬼街》(中篇)/许谋清
《危险的日常生活》(中篇)/皮皮
《四姑》(短篇)/王立
《芜城》(短篇)/赵毅衡
1991年第3期
《米》(长篇)/苏童
《种田大户》(短篇)/高晓声
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大“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影响。与历时8期刊出的26篇“大联展”作品同步呼应的,是批评家们的多篇评论文章,具体如下:
1990年第1期
“新写实小说”笔谈
/董健、黄毓璜、陆建华、丁帆、费振钟、准淮
写实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陈骏涛
众说纷纭“新写实”(文讯)/王十一
1990年第2期
从深沉心态看历史浸润——有感于“新写实小说”/吴调公
写实·现实主义·新写实——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说起/潘凯雄、贺绍俊
中国当代小说思想中的保守态度/木弓
灾变:新潮小说和新潮批评/孙津
1990年第4期
“新写实”的真正意义/汪政、晓华
1991年第1期
写实与形式——兼谈《走出蓝水河》/吴炫
1989年10月31日《钟山》与《文学自由谈》联合召开新写实小说讨论会,1990年第1期刊发“新写实小说”笔谈,1990年2月前后举办“新写实小说”评奖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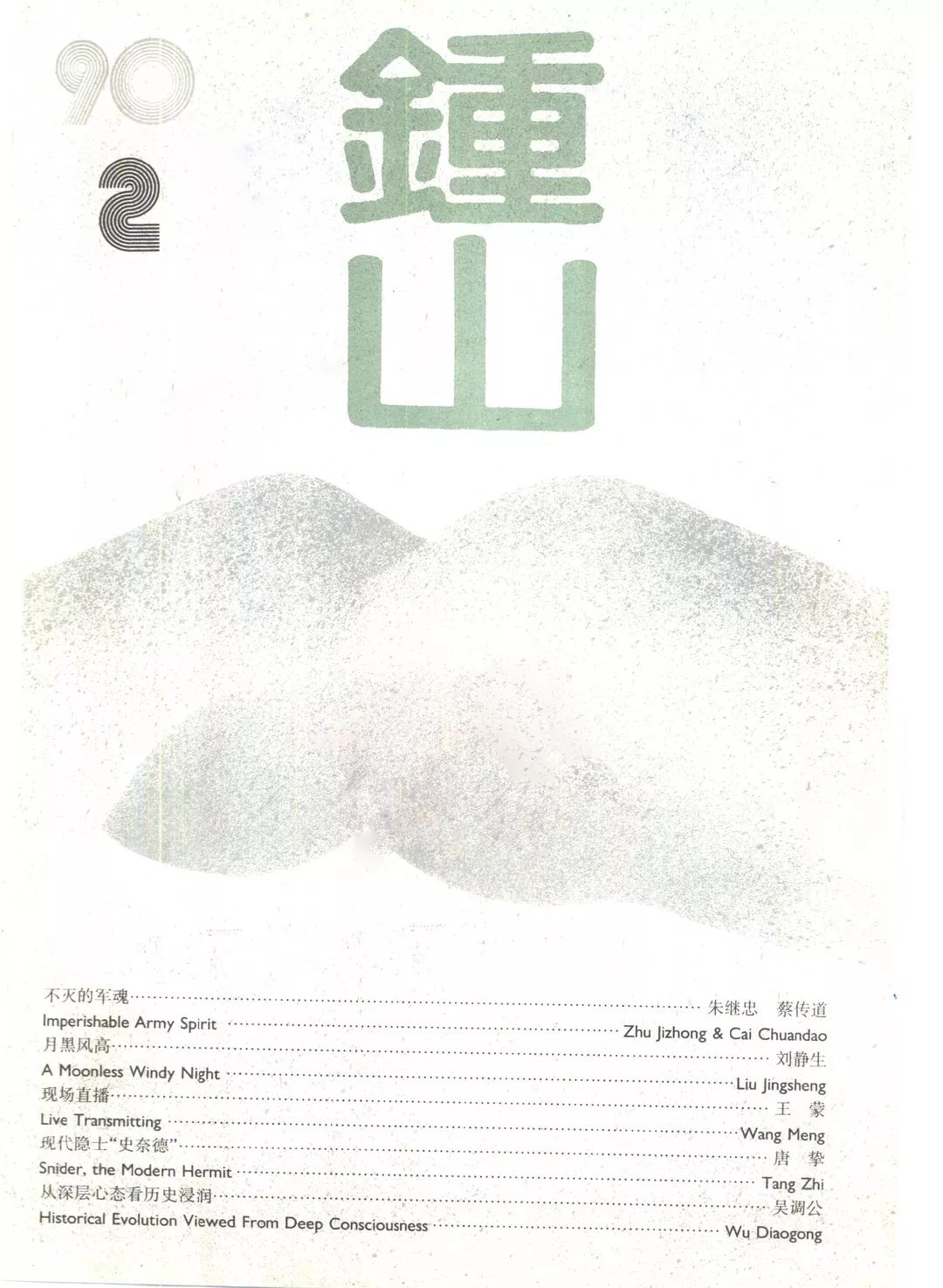


(《钟山》1990年第2期 )
如此多管齐下,“新写实小说”在八十年代末成为继“先锋”(新潮)小说、“寻根小说”后的文坛热点。仅1990年前后,《人民日报》《文学报》《文艺报》《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围绕“新写实”这一话题所刊发的消息或讨论文章就有50多篇。
影响
经过《钟山》的努力,“新写实小说”作为文学潮流或文学倾向,被理论界确认并正式命名。1989年第3期的《钟山》栏目卷首语对“新写实”做出理论界定: “所倡导的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 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这段对“新写实小说”以“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为主要特点的概括一直被后来的文学史所延用。
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对‘新写实’的描述” (第22章第2节)就提到了《钟山》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且直接引用了这段卷首语,并在此基础上将新写实小说特点概括为: “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所谓‘还原’ 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论述新写实小说时则是直接引述《钟山》的观点:“在该栏目的‘卷首语’中从理论上将其创作特点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也作了相似的界定:“它强调的是还原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生活,消解外力加以生活之上的‘本质’或‘意义’,直面生活的原生形态,讲述‘纯态事实’。” 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对这一特点的直接引用或间接转述,都充分地说明了这段概括被使用的广泛性与典型性。
同时,从文学史家的评述来看,“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得益于《钟山》的运作,已经成为定论。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可以看到,‘新写实小说’的提出,既是对一种写作倾向的概括, 也是批评家和文学杂志‘操作’形成的文学现象。” 张永清主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将其作为一个新的特点加以强调:“文学刊物与大众传媒对文学思潮发展的‘推波助澜’作用开始彰显,开始由‘幕后’走到‘前台’,成为推动文学思潮形成的主导性力量。新写实文学思潮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山》等文学刊物与传媒的倾力倡导。……通过媒体的大力传播,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新的文学思潮。”刘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说:“文学期刊策划出一些‘旗帜’来招徕作家和读者,《钟山》是全国文学刊物率先打出旗号的,它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这体现出期刊市场竞争意识的觉醒。”
作为文学刊物,它对于文学影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组织”,使之“流派化”、“思潮化”、“风格化”和“经典化”。《钟山》对“新写实”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的总结和倡导,对这一文学史价值的提供,功不可没。抢先“号准”文学发展走向的脉搏,《钟山》依靠敏锐的文学动态的把握能力,抓住热点、树立旗帜,明确了对“新写实”现象的“冠名”,并将其进一步文本化、学理化、定性化,从而推动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持续数年的“新写实文学”潮流,也奠定了《钟山》自身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中的先锋地位。
作为“新写实小说”思潮重要的发起者、亲历者、研究者,丁帆教授近日撰文《回顾“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前前后后》,对这一文学事件进行了系统回顾,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写实”在今天的意义。
回顾“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前前后后
丁 帆
(来源:《文艺报》2018年7月23日)

丁帆,男,1952年出生于苏州,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扬子江评论》执行主编、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对于亲历过以往文学思潮和文学事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它们进行一次历史的回顾,否则,一切文学史的构成都会有所缺失,同时也会失去它鲜活的生命和斑斓的色彩。当我们重新回顾“新写实小说”发展的全过程时,站在今天的历史潮头之中,我们欣慰地看到那时候的论述至今还保有的理论生命力。当我们将其主要观点重新呈现在大家面前时,猛然意识到,这或许对文学史的重构有所裨益。
“新写实主义”发轫前后
80年代初,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第一次真正受到了危险的冲击。在这种危机面前,有许多明智的作者开始了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方法的修正与改造,由此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新现实主义小说”。
《钟山》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组织策划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大联展”与时任编辑徐兆淮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80年代中后期,我与徐兆淮共同发表了许多文章,后来结集为《新时期小说思潮》,其中涉及到“新现实主义小说”(即“新写实主义”)的议题文章就不下10篇。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但我们始终认为“先锋文学”在中国的土壤中是不会长久生存下去的,它们只能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文本样式存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中,现实主义永远是,也只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然而怎样重新定位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早在100年前,茅盾就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画上了等号,尤其是他对“自然主义”主张的一再倡导,几乎就是把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推向了最高点,这在一个世纪前,不能不说是一次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大事——我一直认为这就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主张的先声。鉴于此,我和徐兆淮一直都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无真正的现实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正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伤痕文学”赋予了中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自然”和“写实”的权力,所以才能让中国文学走进辉煌的80年代,否则,即便是后来“先锋小说”的技术革命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不能没有包含着“自然”“写实”的现实主义,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与被妖魔化了的现实主义进行彻底的决裂。
1988年,《钟山》编辑部召集了北京、上海和江苏的评论家和理论家,以及一些报刊杂志的编辑在无锡太湖召开了一个关于现实主义回归的研讨会,会上大家都针对当时的创作思潮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以及如何回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面对当时现实主义的将要发生的嬗变,我们认为,新时期“伤痕文学”之初,原有的现实主义创作规范仍笼罩于小说领域,其作品只是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内涵上有所重新发现,而形式技巧上毫无突破进展,人们对“现代主义”的名词是那样地陌生和恐惧。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朦胧诗”、“意识流”小说、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等的出现,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才第一次真正地受到了危险的冲击。至此,“不像小说”的小说和“不是小说”的小说便逐渐成为滥觞,迅速占领了文坛的各个角落。那种一成不变的现实主义小说失却了优势,面临着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有许多明智的作者开始了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方法的修正与改造,由此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当新时期文学行进到80年代中期时,随着“寻根”文学高潮的迭起,现实主义小说(那种经过重新修正与改造了的“新现实主义”)与变种的“现代派”小说几乎是并驾齐驱地显示着各自光辉。实践再次证明,创作方法只要不是教条地运用和机械地模仿,都是具有生命力的,它们是推动中国小说前进的两只轮子。
在“寻根文学”与理论界的“方法年”和“观念年”的热点一过,1987年至1988年上半年除了“莫言热”尚未冷却以外,小说界形成了“圈子内文学”,此中备受青睐的是马原、洪峰、扎西达娃、残雪、苏童等所谓“第五代先锋小说家”,这部分作家在纯文学的旗帜下,以新颖的叙事技巧和独特的艺术感觉毫不留情地调侃和蔑视着“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于是,“新现实主义小说”无疑是处在一个受挑战的位置。
写实的诱惑力是恒久的
写实主义,直至发展到以后各个时期不同解释的现实主义,布满了20世纪小说创作的各个时空,“写实”的情结已经成为作家的血脉,它代代相传,亦必须流入21世纪。
尽管新时期文艺理论的第一大战役就是为现实主义正名,但也很难再磨洗出那本来的金子般光辉。因而一旦有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人们的“期待视野”就马上转换过去。那么,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是否就走向末路了呢?从一批又一批不断崛起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者的实质来看,我们以为其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是:第一,他们以人道主义、人性、人情为旗帜,着力表现人的异化母题。第二,在描写人物性格方面,从表层走向深层、从外向内、从“英雄”走向“平民”,从“善”到“恶”。第三,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们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视角,改变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以增强现代意识。然而那旧有的残存意识时时地围绕着整个一代文化人,于是,在向工业化迈进的历史主义与旧有的伦理主义相悖逆的二律背反的现实进程中,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者们在寻找着人的失落与人的悲剧。第四,在形式技巧上,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还有生命力,就是有赖于几代作家不断地吸收和容纳新的表现技巧,它是“新现实主义小说”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生命催化剂。
就此而言,我们试图从人性和人性异化的角度来解释“新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尤其是与“颂歌”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回顾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概括就十分准确,但是,30年过去了,似乎它的生命力还在。
大约近一个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几乎固定了它的运行轨迹。自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宣言以来,大凡小说创作就没有离开过这个轨道,它以巨大的惯性,越过了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时空,成为无可否认的创作思潮,这就是小说的写实性。尽管本世纪出现过与之相抵触的种种思潮和流派,但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写实主义,直至发展到以后各个时期不同解释的现实主义,布满了20世纪小说创作的各个时空,“写实”的情结已经成为作家的血脉,它代代相传,亦必须流入21世纪。
当时我们说,我们不去回顾现实主义的艰难历程,那种回忆也许太沉重太痛苦,而就这些年来的文坛曲折观照现实主义的发展,也许会对小说创作的盲目性有所警醒。8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新潮”、“实验”、“先锋”小说像大潮一般涌来,然而,在空洞的喧嚣之后,她们为我们留下了可数的遗世作品后,悄然隐退了。“新写实”的浪潮又成为文坛的一次大涌动。在“新写实”的大纛下,不仅站起了新一代作家,同时,那些往日从事“新潮”、“先锋”、“实验”小说的作者,亦迅速改变自己,向写实靠拢。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写实的诱惑力是恒久的。
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
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须注入新的内容。现实主义永远无所不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踏勘现实主义新的路径。
无可否认,上世纪80年代带来了小说的技术革命和观念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写实”的灭亡。相反,小说义无反顾地向写实(现实)靠拢。“新写实”小说的崛起,其意义并非在于这个运动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它显示出了小说无可回避、亦无可摆脱的走向。翻检古今中外的小说名著,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小说最终关注的是人,是人类的命运。作为一个永远颠扑不破的母题,它在人类社会的角色中,永远扮演着一个与社会保持一段距离的批判者。于是,每一个时代都缺少不了它忠实的“守望者”——对社会现实的写实写真者。“新写实”作为一个并不遥远的写作所在,它起码预示着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所在。作为一种写实态度的创作,现实主义的宽泛是可包容更多内容的。早期的左拉式的自然主义,以及那些充满着抒情笔调的浪漫主义倾向的描写,几乎都被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亦只有这种宽容的、模糊的、无须严格界定的现实主义概念才使得西方18世纪后的文学璀璨无比,才使得中国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小说呈现出斑斓的色彩,才使得拉美70年代后进入中国的“小说爆炸”时代。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只要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开放体系”的现实,小说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一直认为,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须注入新的内容。纵观从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到90年代的一批所谓返归现实主义的力作,它们只有在注入了新的内涵时,才能获得新的生命。现实主义这棵树如果没有新的生长点,它在新时代面前必然会枯萎。“新写实”如果不是采用了新的观念,对现实主义进行大手术的改造(如视点下沉、非典型化、非英雄化等);如果不是进行了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技术革命(如局部打破小说的有序格局、吸纳现代派的某些变形手法等),它就不会引起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现实永远在向作家呼唤,现实主义永远无所不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踏勘现实主义新的路径。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形式技巧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将“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形式技巧的嬗变单独提出来进行阐述。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主义的形式技巧在20世纪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对表现本世纪人类生存意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们亦不能看到,即便是再纯粹的文学技巧,也终究要表达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内涵,只不过现代主义是通过更为间接的技巧加以表现罢了。即使是存在主义哲学指导下产生的荒诞作品也同样要有主题的意向。就凭这一点,也可寻觅到它和现实主义可能相交的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道路并非是两个永远不可相交的直线运动过程,它们在各自不断延伸的运动中终究会在同一个点上相融合的。就“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来看,它们是在逐渐消融着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差距,打破泾渭分明的临界点,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文体,这才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目标,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逐渐会趋于消亡。两者的互渗互补,将构成中国小说创作的新格局。
“新写实”在今天的意义
围绕“新写实”的讨论已经过去了30年,今天我们回眸这个文学事件,如果能够从细微之处来钩沉历史,尽量回到历史的现场,也许这对文学史料的梳理是有益处的。
当“新写实主义小说”火起来以后,许多人认为这是当下中国文坛的创新,为了证伪,我们开始泼水降温,写了《“新写实主义”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一文,意在溯源与探讨其根性所在。文中提到,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上,中国“新写实主义”的倡导者们与一切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美学观念有着相异之处。在他们那里,真实性不再掺有更多的主观意念,不再有精心提炼和加工的痕迹,而更多的是对于生活原生状态的直接临摹,带有更多的那种生活中的毛茸茸的粗粝质感,创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尽力使自身进入“情感的零度”。其次,在对待现实主义的典型说方面,和一切“新现实主义”的流派一样,中国的“新写实主义”亦是持反典型化美学态度的。正因为他们是生活真实的实录,是带着生活中一切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混合态走进创作内部的,所以,人物意义完全是呈中性状态的,无所谓褒贬,亦就无所谓“英雄”和“多余人”。再者,是对现实主义的悲剧美学观念的颠覆。中国的“新写实主义”在80年代经历了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强大冲击后,基本上摈弃了尼采悲剧中的“日神精神”而直取“酒神精神”之要义,以强大的生命意识去拥抱痛苦和灾难,以达到“形而上的慰藉”;肯定生命,连同它的痛苦和毁灭的精神内涵,与痛苦相嬉戏,从中获得悲剧的快感。在这样的悲剧美学观念的引导下,作家对悲剧人物的观照不再是倾注无限同情和怜悯的主观意念,“崇高”的英雄悲剧人物在创作中消亡。作家所关注的是人的悲剧生命意识的体验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咀嚼痛苦时的快感。
新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对现代文艺思潮的借鉴和融会的浪潮中,绝非偶然。新写实主义小说在借鉴、融会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上,确实已经具备了外部和内部的条件。它发生于新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是新时代的读者和历史观对文学重新选择的结果。长期以来,在怎样看待人和人的价值,又怎样对待爱情、婚姻、家庭上,都明显地存在着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也存在着许多“左”的简单化的政策影响。惟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方能像强劲的东风,吹散长期弥漫在这一领域里的重重的迷雾。但是,光有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的变化,光有种种新思潮的涌入,显然也不能说明新写实主义小说浪潮兴起的内在动因。在新时期的作家群体中,最为活跃且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是一批卓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与前辈作家不同,她们在改革开放的总背景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更多机会接触西方现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法等等。因此,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养料方面多了一个参照系统,有更多的机会在借鉴、融会中完成新的创造。如果我们对新写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作家群体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站在这面文学旗帜下的作家们大都是一些年龄在40岁以下,1987年前后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他们当中固然不乏插过队、当过兵的角色,但更多的却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不管是从现实主义根基上逐渐走向新写实主义的作家(如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李晓),还是从新潮作家逐渐向新写实靠拢的作家(如苏童、余华、叶兆言),他们都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易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吸收养料并借鉴、融会到自己创作中来的作家。运用现代意识,并适当借鉴现代派表现技法,以创作适合于目前中国新读者的阅读需要的作品,乃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共同追求的目标,正是形成新写实主义文学浪潮的根由之一。
如今,围绕着“新写实”的讨论已经过去了30年,而在这30年当中,其话题在不断地延展,它也俨然成为中国近40年绕不过去的一段文学史的表述,翻开这些年来的硕士、博士论文,它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年针对它的阐释文字,今天我们回眸这个文学事件的时候,如果能够从细微之处来钩沉历史,尽量回到历史的现场,也许这对文学史料的梳理是有益处的,庶几在重新掀开它的面纱的时候,可以改变许多人对它先前的片面认知。
当我们重新回顾“新写实小说”发展的全过程时,站在今天的历史潮头之中,我们欣慰地看到那时候的论述至今还保有的理论生命力。当我们将其主要观点重新呈现在大家面前时,猛然意识到,这或许对文学史的重构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