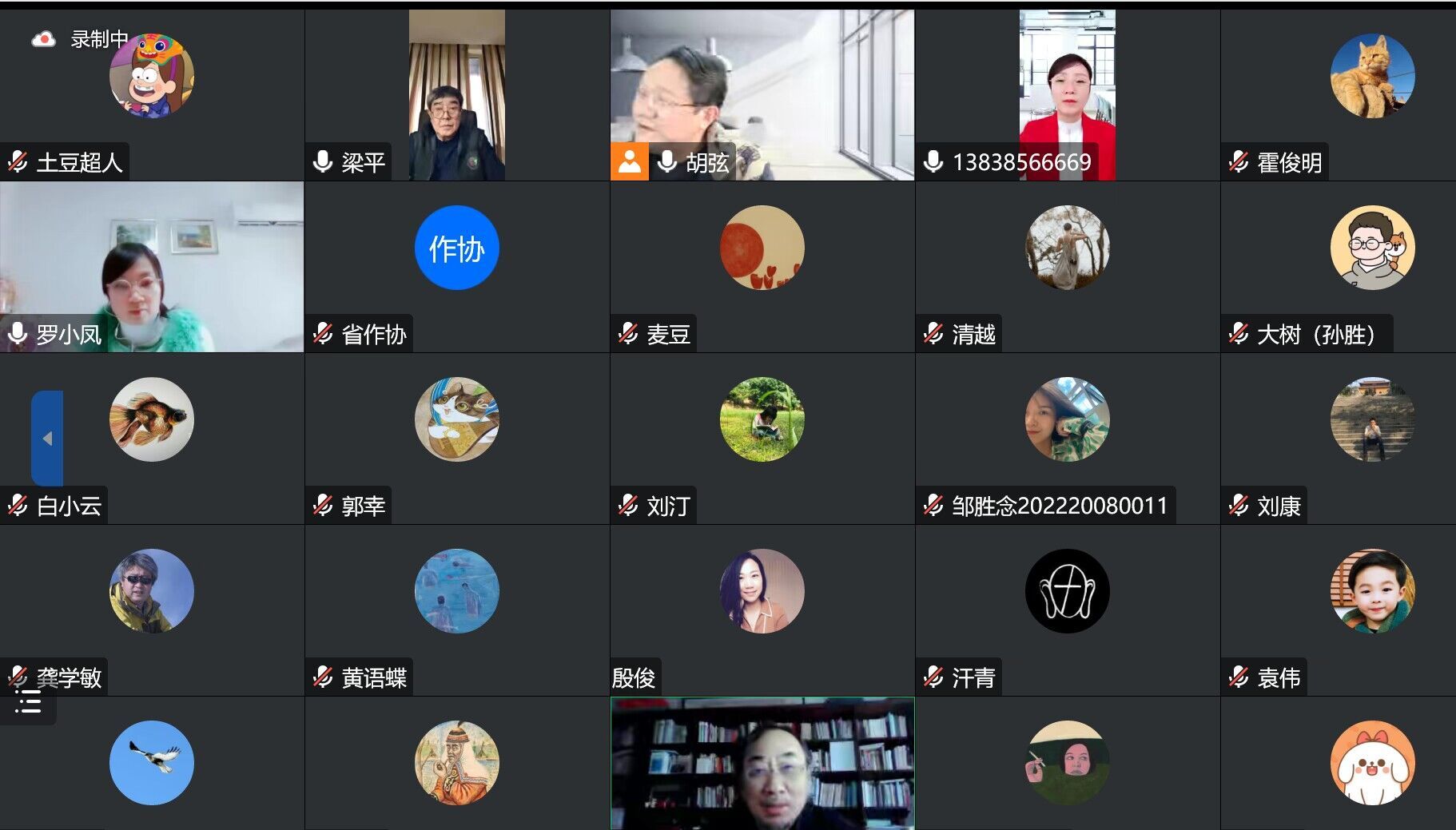
江苏作家网讯 2022年12月19日,省作协在线上举办第五届扬子江诗会江苏青年诗人作品研讨会和大家讲坛暨2022年度扬子江笔会,聚焦当代青年诗歌写作,邀请国内知名诗人、诗评家、诗歌刊物主编参与点评和研讨。
在莫比乌斯环上游泳:诗歌的外溢与进入
为加强江苏青年诗人队伍建设,2022年,《扬子江诗刊》发起江苏十佳青年诗人评选活动,评选名单将于明年公布。第五届扬子江诗会江苏青年诗人作品研讨会分为上下午两场举办,点评的青年诗人大多为入围十佳青年诗人终评名单的青年诗人,会议采用点评专家与青年诗人一一配对的方式,对青年诗歌进行针对性点评和改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出席研讨会并代表省作协向各位专家表示感谢,他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推动全国诗歌界更加关注江苏青年诗人的写作实践,提升他们的创作水平,共同助力江苏青年诗人的进步成长。省作协副主席、《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和《扬子江诗刊》编辑部主任白小云分别主持研讨会。
“在莫比乌斯环上游泳”是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孙冬对刘康诗歌的形容。她认为,刘康的诗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抒情叙事诗,常常通过使用异域的地名和人物、在叙事中制造时空错位、创造超现实场景等方式,为熟悉的日常带入陌异感,因而虽起于琐碎的世俗世界,而终能抵达超验的想象,在虚实交叠的界面上,思考死亡和存在的终极问题。在刘康的诗里,生活和读写融为一体,此刻和彼时、自我和他人、世俗和超验、此处和外邦无限连接,仿佛无止境的莫比乌斯环。但缺陷在于莫比乌斯环是闭环,可能会因为过于流畅而杜绝了外溢。
孙冬在点评中谈到经验问题时,反对对生活经验做窄化理解,赞同刘康将阅读经验乃至“超验世界”纳入真实生活经验的努力。事实上,本次点评的青年诗人中,突破日常时空和偏重抽象写作的不在少数,但这类写作往往存在类似问题:或过于封闭,或难以进入。如何在个人体悟与公共经验之间建立沟通的秘道是他们面临的共同课题。如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点评殷俊作品时,肯定其写作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和很好的语言底色,但建议她持续打开诗歌中的生活世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成都市文联名誉主席梁平看到了贯穿茱萸诗歌的写作线索是痛惜曾经影响过自己而正在消亡的人文情怀和精神谱系,期盼能够在自己的诗歌世界中让它们永生,从而寻找真正的生命和精神同道,但梁平仍然希望茱萸可以继续尝试拓宽自己的诗歌领域。北京大学教授唐晓渡在点评李看的诗作时指出,李看的诗在柔和守弱中自有一种警醒和坚定;其语言罕见的生动自如,表明了她对当下即刻的美——那“枝头上的花”的极度敏感和瞬时赋形能力。在她对“自己的样子”的倾心追慕中,隐藏着一个诗人最可宝贵的天赋,但需要警惕的是以此自狱。“所谓‘自己的样子’,对诗人来说更多意味着敞向未知的不断的生成。”
黄语蝶、郭幸和秦三澍等青年诗人的诗歌则呈现出更为隐晦幽深的面貌。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形容秦三澍是“语言的炼金术士”,其语言实践看似狭窄、实则幽深,他的诗歌意象非常饱满,而且意象自身就凝结着理想色彩,有一种蕴藉的、朦胧的诗歌关怀,再加之叙述逻辑的跳跃和省略,意象并未完全安置在逻辑情感中,从而增加了解读的难度。《莽原》副主编张晓雪认为黄语蝶是一位内心丰富、专注、敏锐的诗人,她敢于进行写作实验,将意象、情感、场景、细节铺陈得十分绵密,有些诗句甚至横跨整个页面,她的诗往往流露出困惑感和异质性,抽象感强烈,但要避免文字呈现出过度的室内感。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清华也肯定了郭幸诗歌中的生发性,认为她的诗里有精细的个人世界和内心生活,感情丰富但不撒娇,《苏康码》有明晰的现实感和生活感,《影子》《哑巴》等则更为现代:意思不明确但相当丰富,诗歌主体与作者本人构成了镜像关系。但张清华指出,“写诗如同建造园子,要先提供确定的入口,再将丰富的景观隐藏其中”,建议郭幸将潜意识的设置深度和诗歌的隐喻关系与现实的确定性的东西连接起来,来到公共经验可以抵达的地方。
青年女诗人记得则经历了一条从具象写作到抽象写作的转型之路。在《人民文学》编辑刘汀看来,记得的写作具有女性意识又不局限于性别,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细小,写作前后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逐渐走向了不那么具有现实感的抽象书写。但刘汀建议,在风格转变过程中,尤其应避免意象过于虚化和松散,诗歌逻辑要遵从现实世界的既定事实,否则其超拔性和先验性往往是立不住的。
写一首诗也是在发明它的写法:诗歌的叙述和语言
另一部分青年诗人擅长于日常生活和具体事物中提取诗意。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黄梵就将袁伟的诗歌归为“物象诗”,袁伟将视线收窄到事物之上,重在挖掘事物的隐喻关系而非象征关系,通过事物的特性关联其他,这类写作的关键点在于能否找到独特的关联点,而袁伟正是由此证明了自己的洞察力。但不足的是,袁伟重视意象空间的开阔而忽略了语言空间的探索,语言的留白处理不到位,叙述线条过于连续,缺乏跳跃。
“如何在保持自然通透的诗学风格的同时,赋予诗歌语言足够的张力和弹性?”《十月》主编助理谷禾点评大树作品时,对这一问题作了集中阐发。谷禾认为,大树的诗歌写作扎根于当下和自我,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其语言自然通透又情感丰沛,但“诗歌同时兼具重新发现甚至发明语言的重负”,这样的写法更需要鲜活的细节来增强整体的丰富性,处理好呈现和留白的辩证关系,让作品生发出最大的诗意。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胡弦点评时指出,“写一首诗其实也是在发明它的写法。”扬州大学教授叶橹评价宗昊的诗体现出对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朴实诗性的表达,他的想象力具有梦幻般的魅力,其诗歌语言不追求所谓的现代性的奇形怪状,而他所传达出的思绪与诗情却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人严肃而深邃的生存思考。无锡市作协主席黑陶赞赏许天伦的叙述沉稳细致、从容不迫,善于由日常进入,再超越日常,诗歌内部的时空感十分开阔,能看到个人生活的影子,有很强的诗歌感悟力和表现力。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在李海鹏的《转运汉传奇》里看到了冯至的影子,这首改编自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的诗歌,叙述时做了人称转述和语体转换,具有微妙有趣的节奏感。扬州大学教授罗小凤认为张昭琦能从小场景、小情绪上升到存在格局,同时也做了诗体形式的探索,语言有种梦呓般的感觉。
同时,语言和叙述恰恰也是制约很多青年诗人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文学港》主编荣荣看重里拉诗歌中的“寂静之声”,认为她的诗有独属个人的生命体验,有温暖的质地和恬静的角落,但有些语句表达不够简洁。诗人叶辉认为邹胜念的诗歌已经具有一定的成熟度,但目前仍然局限于个人感觉层面,诗歌语言锤炼得不够,随感式的叙述略多。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看来,汗青的写作体现了Z时代的特点,内里充满个体的紧张创伤和被剥夺感。汗青善写场景,写空间,写微型叙事,但文体意识还需要加强,情感也过于悲凉,缺乏控制。
语言之于诗歌,在于深化“诗意”,生发“陌异”。《青春》主编李樯尤为喜欢杨隐的《提瓜记》,就是感到这首诗对事物秘密的把握与呈现出人意表,但杨隐的另外有些诗——无论词语、意象的选择,还是主题、情感的表达,则未见新意,诗歌的叙述艺术需要加强。泰州市文联主席庞余亮喜欢邹黎明的《天刚有亮意》,但认为邹黎明的部分诗歌做了过多减法,整体不够饱满,用词和主题也具有惯性。《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认为清越的诗歌是比较开阔的写作,她借助装置艺术探索诗歌表达方式,勇于跨界,努力寻找自己的精神原型,其中有些诗句字数完全相等,这种方式可以尝试,但不宜泛化。
青春在未来等待写作者:大家讲坛聚焦诗歌与青年
19日晚,第五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以“诗歌与青年”为主题,延伸探讨青年诗歌写作问题。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温潘亚,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诗人傅元峰和诗人庞余亮、黑陶、胡弦参与论坛,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王尧主持讨论。
谈到青年诗歌写作,傅元峰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诗歌文化,认为80年代的校园刊物作为新时期文学底座的一部分,有着鲜明的亚文化血统;这代人大学毕业后,又将校园诗歌写作实践带向各个角落,但评论界往往忽略了青年诗歌中的亚文化部分,尤其是独立音乐的创作整体上被忽略了。何平认同傅元峰的判断,在他看来,要全面判断青年诗歌写作的价值,不能仅仅局限在诗歌领域中,早年的诗歌写作激活的不仅是语言和审美,更是思想,很多青年写作者转而进入其他领域后,早年诗歌写作的思想积累仍然保留了下来,在其他领域继续被激活和运用。
“大学时代应该是诗人辈出的时代,这个年龄段是最容易、最愿意、最喜欢写诗的时候。”一直在中文系教学的温潘亚在共同怀念80年代校园写诗风潮时,感慨近年来学生已经很少写诗了,“一切都那么平静、理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庞余亮和黑陶都是在大学阶段开始了诗歌写作。黑陶的第一首诗发表于35年前的冬天——1月7日发表在《苏州日报》,他深受鼓舞并一直坚持写作到现在。庞余亮分享了自己诗歌写作的几个阶段,直到1992年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诗歌,这之后开始寻求改变,直到1995年发生蜕变,在《底层生活日记》《理想生活》等作品中,“将生活中的痛苦、不甘和失落都写进去了”,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到1998年以后创作量再次削减,直到2008年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深度反思后,又迎来了新的创作高峰期。
“2016年后,我又进入了瓶颈期”,庞余亮说,“我所以坦诚地分享我的诗歌成长史,是希望大家从我身上思考如何维持创作的连续性,避免止步不前。”因而,在探讨“青年与诗歌”的过程中,与会专家逐渐由此生发,思考“为什么新诗好像不支持人变老?”傅元峰观察发现,很多中国现当代诗人到了中年以后逐渐不再具有旺盛的诗歌创作力,他们最好的作品都是青年时代写出来的,但反过来看,也许晚年创作能力的衰退恰恰说明早年的写作已经隐伏着危机。他以叶芝为例,“叶芝是一位成功变老的诗人”,他早年的写作十分圆熟,反而到了晚年才越写越清澈,越写越激荡,到了晚年才从知识和经验中走出来,达到语言的纯粹境界,“这就是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在晚年写作中产生了青春气息。”
“青春”作为写作的纯粹性被重新提炼出来。胡弦结合自己的经历也对此作出了阐述。胡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直到有一次偶尔接触到《诗歌报》,认识了更多的诗歌文本后,开始了更加自觉的写作阶段,中间也遇到过瓶颈,“诗歌确实是青年人的事业,但现在也很重要。如何突破中年写作?”胡弦认为,自己更多是把当下写作当作未来写作的序曲,“诗人对自己的未来还是要带着一点盲目的预感,青春在未来等待写作者。”(俞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