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讨会现场
江苏作家网讯 2022年11月13日,省作协在南京召开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作协主席毕飞宇,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江苏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以及国内知名批评家等50余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出席研讨。会议由丁捷和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主持。

王尧著作

吴义勤
“要特别祝贺王尧作为学者、教授、作家的多重身份。”吴义勤在讲话中说,“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表面上很温柔,但他的思想其实是很硬的。”吴义勤重点谈了对《民谣》的感受,认为《民谣》体现了王尧的纯文学理想和精神,既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传统和80年代的先锋传统,其对世道人心的把握又有社会现实内涵,展现了王尧的思想野心和思想能力;《民谣》在叙事创新和艺术探索上卓有成效,呼应王尧自己提出的“小说革命”,包括方言的使用、叙事的松弛、时空的处理,“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

汪兴国
汪兴国回溯了王尧的学术和创作历程。王尧从上世纪80年代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开始,到后来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通过其学术实践拓展并推进了自身学科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与时代文化思潮进行了全方位互动。他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他将创作与研究融为一体,其散文无论是对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命运的关注,还是对“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的审视,书写的都是对“历史”与“自我”的理解。2020年,长篇小说《民谣》问世。经过几十年的酝酿,有种瓜熟蒂落般淋漓而丰沛的元气。
“民谣,正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个体,来自于日常。”以汪兴国的这段话隐喻王尧的研究立场,也揭示了研讨的意义:王尧是主体自觉意识很强的研究家和创作者,与会专家畅谈自己心中“这一个”王尧,其意义或许自能指向“久远的未来”。

丁捷

汪政
乡关何处?《民谣》是一代人的记忆之书

程永新

张学昕(线上参会)

何向阳
“二零零几年我跟王尧在西安参加活动,谈了很多文学的事情,他羞涩地说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对我讲了创作念头,我想不就是一部成长小说吗?”《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回忆。念头里的小说落于笔端,2020年,《民谣》出版。王尧把成长小说的元素隐在背后,“是一部在精神世界建立了小说价值观的小说”,程永新说,“对记忆和历史的处理达到了极致。”
“历史记忆终究是个人记忆”,在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看来,“《民谣》体现出王尧一种特别的记忆转向,从大历史转向个人史,进入了人性、情感、生命的微观记忆。”
“《民谣》的第一个字就是我。”何向阳也从个人史角度展开分析。她指出,史铁生、王安忆等50年代作家多携个体史登上文坛,而后再由我及他;与此相比,60后在小说中的自传是罕见的,他们一直将“我”安放在他们之中。这个意义上,《民谣》向个体历史的逆行具有重要意义。

梁鸿鹰(线上参会)

陈晓明(线上参会)

文贵良
“《民谣》处理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认为,王尧为自己出生、生活的村庄立传,把存在于老百姓眼中的有真凭实据的历史还原出来,“反映了苏北乃至中国在特殊历史阶段所承载的历史”。
“它是50年代、60年代两代人的记忆。”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认为,《民谣》把20世纪最为深刻的、每个人的生命记忆一点一滴地写出,用平淡的方式写下了沉重的历史。
平淡与沉重的张力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曾以《宁静与压抑》为《民谣》撰写评论,从隐喻系统的运用、成人化的少年视角、多层次的人性平衡和麻绳型叙事等角度,探讨“平静的语言怎样能够表现一种沉闷的压抑的生活?”

孟繁华(线上参会)

徐勇

刘琼(线上参会)
而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看来,这种平淡“不是置身度外的冷漠,而是经历过后了然于心的淡然。”王大头看似漫不经心的讲述,日子看似云淡风轻,但内在的紧张几乎没有消失,平淡语调暗含的司空见惯因而给了荒谬年代以致命一击。
“这种轻描淡写当然只是一种姿态。”孟繁华提醒王厚平是神经衰弱患者,病患身份的“人设”对讲述者至关重要。王厚平经常做梦,对他来说,他遭遇的不是梦境,而是梦魇。“这个细节不仅符合王厚平的病患者身份,也是他1972年间的少年记忆,这一个人记忆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这是《民谣》不动声色的力量所在。
放到文学传统中来看,厦门大学教授徐勇将之归入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抒情书写传统:反情节的结构设置,但细节又特别凸显。“从五四新文学以来可以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乡土写作脉络”,《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进一步指出,其中主要的两条:一是鲁迅开启并辐射开来、带有启蒙特征的乡土写作,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抒情叙事。“王尧的乡土创作既有沈从文的柔情,深得其叙事美学之精妙,同时从思想和灵魂气质上更接近鲁迅的热肠。”
《民谣》综合了各种笔法、语调、节奏、修辞,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语言和风格。何向阳认为“以《民谣》为标志,王尧也是小说革命的实践者,更是将小说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家。”但孟繁华对此态度保留,在他看来,小说在形式上的革命到了“后现代小说”,业已终结。“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民谣》作为小说,它为历史叙述打造了另一幅面孔。在小说创作面临极大困境的时代,这已经足够了。”
重返80年代:文学研究不能缺少文学的感觉

丁帆

郜元宝

金理(线上参会)
在南京大学教授丁帆看来,王尧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他的当代作家系列对话,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同时以史家眼光选择对话对象,暗含哪些作家进入文学史序列的筛选过程;二、他是多文体的文学创作实践者。区别于五四时期从思想和启蒙角度的进行小说革命,王尧提出的“小说革命”着眼于小说的技术革命、文体革命;三、学术研究方法方面,对六七十年代特殊时期的研究以及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社团研究用功颇深,近年又带领苏州大学海外汉学奇峰突起。
这些特点让王尧成为辨识度很高的文学研究者,他的入场姿态也一度让一些同行批评家“不太适应。”“我最初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从来不认识作家,但王尧最初就要求批评家跟作家面对面交流。”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说,“我们那个年代步入文坛的人首先研究文本”,但王尧“哪怕是当代作家的评论也要先讲几个文学史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正宗。”
郜元宝说的是近年文学研究界所谓的史学转向,而王尧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向来是高度结合的,“他最初研究现代散文史,后来研究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文学历史,最近又进入到现代文学的历史。从历史、文学史到文学批评,是王尧在研究上走的一个很清楚的路径。”郜元宝说。
如果将“重返”作为王尧学术研究的标志性动作,首先引起注意的或许就是他“重返历史”的努力。
“他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他提出的‘向后转’。”复旦大学教授金理说,“他提出我们可以重返80年代,但不能无视已有的经验、共识、教训而往回倒退,他把近几年一些研究中所出现的价值判断倒退这一现象命名为‘向后转’。”

刘大先(线上参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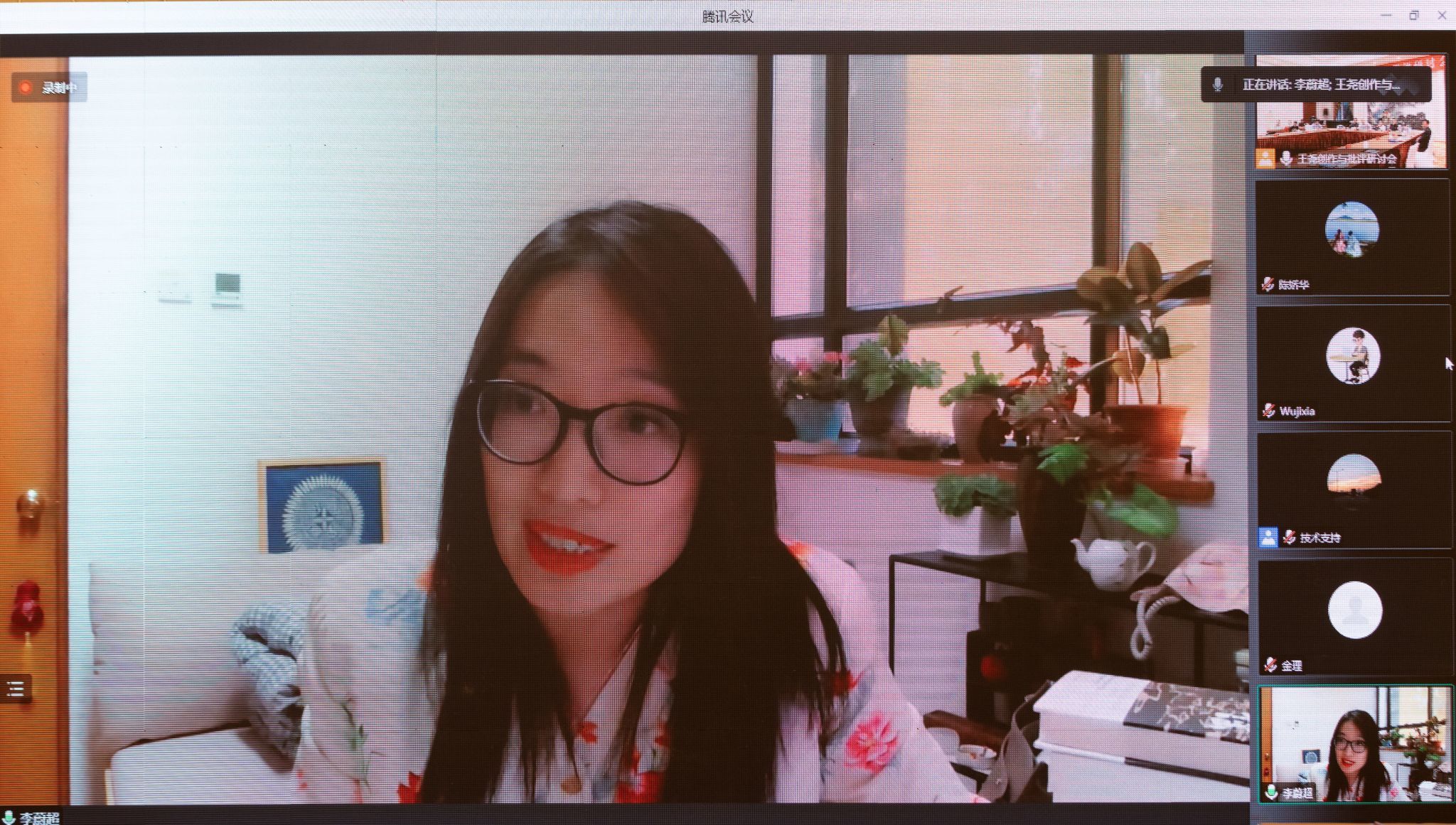
李蔚超(线上参会)

黄发有(线上参会)

洪治纲(线上参会)
王尧的重返不是盲目地“向后转”,而是有着自己的史识和方法论。“他关于文学史的过渡状态和关联性研究特别有洞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说,王尧反思了文学史叙述的断裂性和延续性,明确指出过渡状态是延续未完成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中间状态,也正是活力和生机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形容为“一种时间的空间化与时代的缓行”:一方面,他借助人物的回忆、声音和肖像等来恢复历史的空间感,他提出包括过渡状态、分层现象等文学史关联词,再造空间式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他的历史研究并不急于做大的判断,对历史过渡和持续的感知要超过对断裂的指认。
“重返历史”并非王尧唯一的“重返”动作,“时间的空间化”同时也是“重返现场”的努力。山东大学教授黄发有补充提到,在《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中,王尧提出编辑出版与批评的过程在文学生产过程中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或许也是他重现历史现场的某种尝试。
主张批评家与作家对话,出版《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把作家引入校园,让作家跟师生进行直接对话;从史实建构出发思考当代文学学科和文学建制——在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洪治纲看来,王尧的学术实践带着明显的发生学思维,“但别有意味的是,他的研究文章又不是疯狂的理论阐释,而是充满着感性的、直觉性的表述。”

李松睿(线上参会)

韩春燕

王春林

王兆胜(线上参会)

陈汉萍(线上参会)

张燕玲(线上参会)
王尧对文学研究的复杂性有充分体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李松睿注意到,他在从事研究时很少使用理论工具,“他认识到简单的理论框架对历史复杂性的遮蔽。”《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认为,“他能够有高度,还真正能够在细处下功夫。”汪政也认为, 王尧的批评见人见文,以同情之心看人,以体悟之心看文,以智慧之心言说世道人心与存在之理,以汉语之美解读他人文本,有现代人文学科的自觉意识。
“大局和细节并重,注重时代、社会、历史变化,又很少停留在空论,比如对文学研究物料做得很细,是细读、精读、慢读的典型例子。”《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王兆胜说。《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也注意到, “不同于一般学者对思想问题的反复诘问,王尧老师总是温和、细腻地呈现复杂纠结,并把生活融入其中。他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但又是温和地展现的。”
诸多“重返”指向的或许还是重返文学、重返生活。作为老朋友,丁帆与王尧私下交流时有这样一个共识,“一个学者如果没有文学的感觉,那么他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就是不及物的,他的文学研究是有隔膜的。”文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学本质性的东西,是批评家王尧总的旨趣,他致力于“把抽象的概括和灵动的、感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很欣赏王尧的艺术直感,“一般来说,文艺创作都会强调艺术感觉的重要性。但其实,文学批评也是需要很好的艺术直感的。王尧之所以能够从文学批评出发,走向更加广泛的文艺创作领域,与其良好的艺术直感是分不开的。”
正因如此,“王尧的评论很多以学术随笔面世,他让深邃广博的研究回到了围炉漫谈式的学术交流,讲起故事也是徐徐道来,从容自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
日常的弦歌:散文是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

张新颖(线上参会)

张福贵(线上参会)

张莉(线上参会)

杨庆祥(线上参会)
随笔散文在王尧的研究和创作中均占有重要位置,他曾说,现代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王尧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雨花》《上海文学》开设专栏,出版有《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等多部散文作品。
“我特别注重的是他关于中国现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创作叙述。”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说,“通常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看成是文学史的边角料。”但张新颖看来,王尧的系列散文试图把百年来现代汉语沉积堆叠的东西挖掘出来,“这可能是比我们认为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文学史。”
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对王尧的散文作品进行过文本细读,以《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为例,他重点解析了前半部分关于现代文学史的叙事,对于这样一种间隔的历史,王尧采用了历史文本与自我感悟连缀的叙述方法,如《“寒夜”里的“青油灯”》通篇来自巴金的散文作品,在文本和视角间不断转换,使叙述对象有了立体感和想象的空间。王尧的散文注重从历史叙事中展示个人历史的对比性,并注以深刻的思想言说和诗意的叙事语言。
但同时,张福贵也注意到王尧在历史叙事中的选择性与模糊性,“他花了八节文字记述1949年前的郭沫若,对于他的后半生则交给历史评价。”比照李蔚超对其研究思想的论述,或许可以产生新的认识——“对于人物的突出让王尧的文学史观保持在动态的、必然中的偶然性,也就是他所说的悬而未决的文学史。”
“‘所见者大、取材者微’,王尧将经验书写的集体性和个人性进行了结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继续阐释认为,“所见者大”在于王尧有浓厚的知识分子关怀和深厚的历史感;但同时,他摒除了很多学者外在的、说教的视角,所选的是一个内在的、小的视角,做到了细节的充实和丰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形容这一特点为“执拗的低音”。杨庆祥认为,王尧是“要把被时代的高音所遮蔽的微弱的声音、可能被我们遗忘的声音充分释放出来,这种声音又跟记忆密切相关。通过这种声音,他不仅勾连起了同代人的历史记忆,也唤醒了我们这些非同代人的历史记忆。”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染有自己的指纹

郭冰茹(线上参会)

贺仲明(线上参会)

黄平(线上参会)

吴俊(线上参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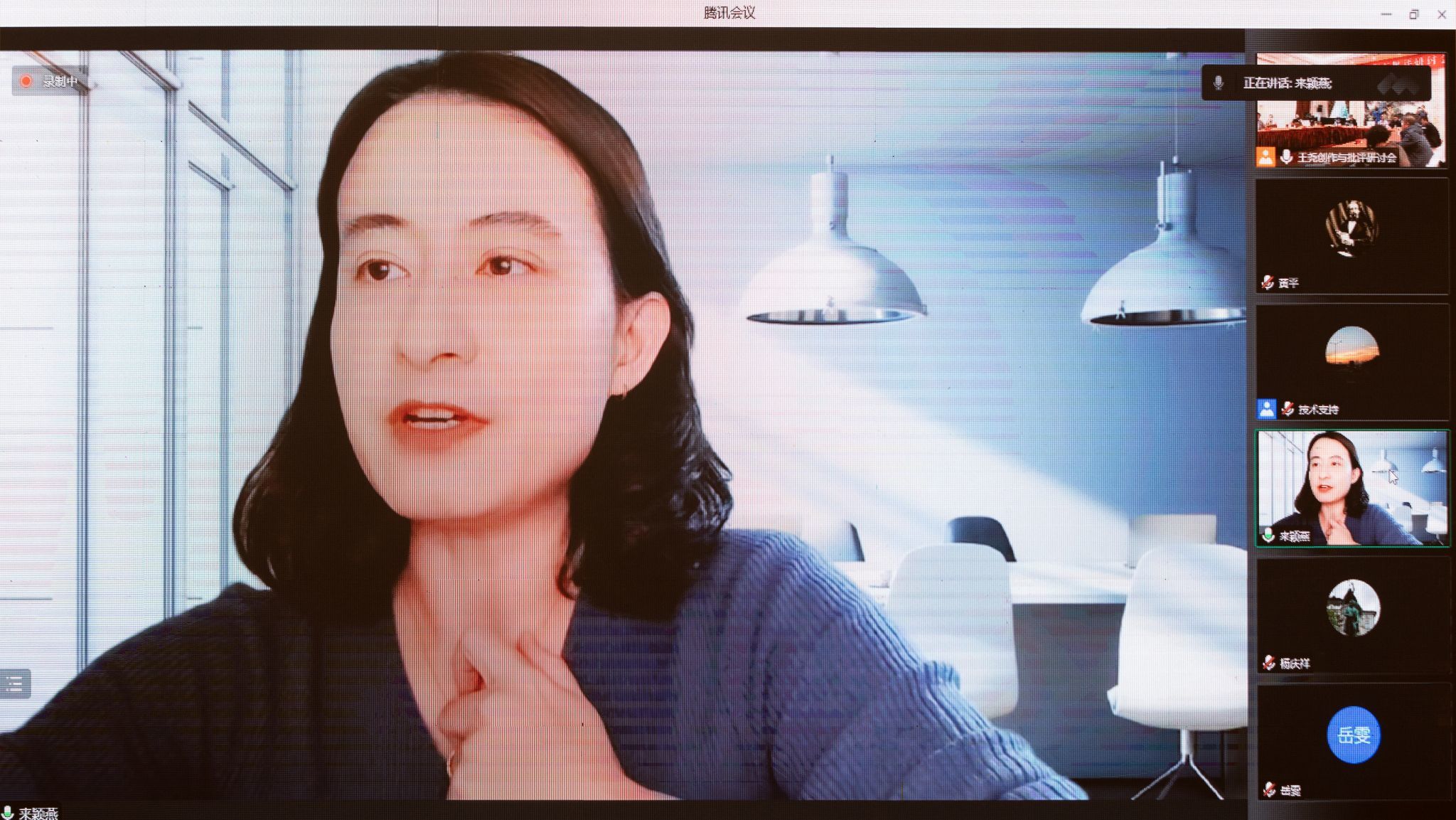
来颖燕(线上参会)
按体裁划分固然便于梳理总结王尧的文学成果,但这大概也恰恰违背了王尧的文学实践。看重“文学感觉”的王尧在创作与批评之间来回跳跃。“文学研究、口述史写作和小说创作,看似属于不同的领域,但王尧通过对叙事本身的关注把三者联系在了一起。”中山大学教授郭冰茹说。
“王尧的学术研究、文学评论和创作具有很多一致性。”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列举,比如对人性的肯定和对人类美好感情的追寻、诗化之美,以及历史思考和批判精神。
“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有两股相反相成的潮流:其一是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学科化,并走向科学化;其二是评论家向作家的转型。”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看来,文学不能被科学化的部分,才是文学最为精髓之处。在这个意义上,王尧的创作转向尤为重要又顺理成章。南京大学教授吴俊也认为,“王尧的实践先于他的理论,代表了80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一个跨界的新的文学时代。”
“我们会说,他拿起了写小说的笔,是一种跨界。但我越读他的作品越觉得,许多界线在他眼里是不存在的。”《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认为,更为核心的其实在于王尧对文学属性的界定——不论哪种文体,必须染有作者自己的指纹。

张光芒

初清华

饶翔(线上参会)

张涛(线上参会)

房伟
“《民谣》的第一句话对小说特别重要,‘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在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看来,只有找到了这句话,才能为整个小说的叙事建立起时空伴随的基调,作为叙事者的现在的我不是坐在码头上的我,那个孩童也并不必然就是我的童年,其实是另一个主体。“王尧特别警惕和担心的是久而久之丧失了我与世界的连接能力。包括王尧看他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力图唤醒其主体性,使研究对象也具备一种时空伴随的定位,他不想概念化、静止地看待研究对象。”
这种主体性确认焦虑或许解释了郜元宝所说的——王尧的研究有一种“紧迫感”,他希望追问“我们”这代人在历史上能留下什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初清华曾是王尧的学生,在她眼里,“王老师作为批评者一直试图在文学史中建构自己的位置。”
“他认为文学批评也是一个批评家的自序传。”《光明日报》编辑饶翔说。
可能因此,有时他不惜把话说的旗帜鲜明一些。“王尧的研究有很强的命名能力。”吉林大学教授张涛注意到,比如关于小说革命的探讨和判断,对当代文学过渡性的看法等。“王尧擅长对文学史现象总结、提炼,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是重建了自我与历史的联系。”苏州大学教授房伟说。

岳雯(线上参会)

丛治辰(线上参会)

何平
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能否染上“自己的指纹”——其实这一问题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的思考,从而指向的是文学的根本功能。
“王尧一直在思考的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兼具知识分子和文人品格的人,如何在这个极具不确定性、充满历史焦虑的时代打好自己的精神根基,建构完整、独立的人格形象。”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岳雯认为,他的写作始终根植于这个根本问题。
“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不能完全说没有思想能力),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内心应该还生长和挣扎着另外的的生命迹象。”北京大学教授丛治辰引用王尧在《我们的故事是什么》里这段自我剖析,“我觉得这已经是评述他关于那样一个大时代底下知识分子的细小生活和个人选择的最好论述,可能也是这部书的学术性、文学性以及对今天生活意义的最好发言。”
此时,不妨挪用王尧的研究旨趣,将王尧本人也置入“时空定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就把王尧“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置、文学批评传统包括一代人的思想背景下”来认识。何平认为,王尧属于新三届毕业生,身上具有他们一代人的特点。乡村与城市、边缘小城与中心城市等,是他持续关注的问题。乡村记忆对他们这代人的精神成型有怎样的影响?从他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可见一斑。
或许人人都在寻求自己安身立命的真正家园。乡关何处?之于现实中的王尧,是自己出生长大的苏北村庄;之于学者和创作者王尧,则是他深深怀念的知识分子精神,是那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学场域。

王尧
若将这场研讨也视作文学场域,王尧在致谢词中再次实践了自己建立对话关系的主张。“坦率讲,我内心有非常多的困惑,转换文体恰恰是因为我对很多东西不了解,所以尝试用其他方式询问一些问题。”王尧自认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但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并不想“寻找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定位”,“只是以历史的参照反省自己的薄弱和平凡,知道自己如何存在下去。”

毕飞宇
“作为王尧小说的读者,我还是要谈两点看法。”毕飞宇在总结发言时说,一是“知识分子写作”和“知识分子的写作”的区别。“老实讲,好作家都应该是知识分子写作。反过来说,许多知识分子的写作——我指的是文学创作——是令人生厌的,因为欺负人,因为他们读书知道了一些思想资源的知识,想尽办法在作品中呈现。”而最可贵的是一个作家拥有丰沛的思想资源,并将其转化成他的叙事和描写。此外,毕飞宇引用普鲁斯特“我完全可以把眼睛闭起来重新处理生活”,强调记忆的重要性——“处理记忆就是处理生命,处理记忆就是处理历史。”毕飞宇认为,王尧在他的思想资源的推动下,打开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修正了他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具有文化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新锐作家,“我为我们江苏省作家协会、为江苏文学涌现出这样一个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小说家而倍感欣慰和鼓舞。”(文/俞丽云;图/于邦瑞、丁鹏)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