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薛晨鸣,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科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历史记忆谱系研究与叙事伦理召唤——刍议沈杏培《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
内容提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独异的形态嵌入了数代人的生命轨迹,这不仅召唤着作家以如椽大笔书写民族记忆,也呼唤着研究者对既有创作进行批判性的整合透视。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忆书写是当代小说版图中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新时期文学中蔚为大观。沈杏培教授的新著《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以其博士论文为底稿,推进了自新时期至新世纪四十余年小说的历史记忆谱系研究。《论稿》在建构历史记忆叙事展馆的基础上,推动批评者和创作者的主体对话;在反刍民族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呼唤建立新的叙事伦理,以此实现人类“类经验”转化,书写中国文学的大气象。
关键词:《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历史记忆;叙事伦理;“类经验”
沈杏培教授的新著《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下文简称《论稿》)以其博士论文为底稿,经过十年打磨,2022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殊荣,全书以新时期至新世纪四十余年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作为研究内容,通过历史学、叙事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全面梳理新时期小说如何讲述或想象历史记忆问题,体例完整清晰,既立足本土作家的文学叙事,细致呈现作家们建构历史过程中的诸多文学风景,又在世界文学坐标系下寻找中国作家历史书写的特点和局限;既体现思想性、当代性和世界性的融合,又有青年学人对学科重大问题的理性关切,与当代主体对历史的深情姿态。
一
有情的叙事:文学如何呈现历史印痕
当代文学对历史记忆的追溯和书写,构成了特征鲜明的小说群像。此处言之的历史记忆,着重指向不同代际作家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体时代风貌的记忆。这段历史记忆之所以持续点燃作家们的创作热情,是因为它距离当下人的生命体验太过切近,形塑了几代人的生命印记和人生走向,然而载入历史的瞬间又是如此迅速,还未给身处其中旋即又被驱除出去的亲历者以思忖的缓冲空间。于是,作家们不断通过作品反刍,从自己支离破碎的既有记忆中打捞那段历史记忆的剪影,将个体经验投射到小说创作之中,舔舐父辈或自身的伤口,努力描摹出曾经切实经历过的时间是如何推搡出现今的人生线条。由此,历史记忆小说群像汇集了诸多作家的记忆体验,不同印记重重堆叠,勾勒出后代触摸这段历史记忆的基本轮廓。当小说引发读者共鸣,抑或给后来者窥视彼时的窗口,小说建构或想象的历史记忆也就进入了民族集体记忆的范畴。作为民族延续和代际更迭中集体记忆的隐晦保存者,历史记忆小说及作家叙事模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历史记忆小说的整体考察,也即意味着以审慎和悲悯的态度对待本民族历史。
由此,以历史记忆为中心的文学问题进入沈杏培的研究视野中,《论稿》正是对此思考的回应之作。沈杏培以历史记忆和叙事作为进入论题的两个关键词,分别从书写原点和创作路径的双重维度,对历史记忆小说进行整体性的动态把握。鉴于这段历史之于民族的精神创伤,以及政治上的定性,既有研究往往只阐释其“存在之由”,沈杏培沿用王国维的治学方式,执着追问其“变迁之故”,引入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这段历史记忆放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坐标中予以观照,以求真的治史态度,探照这段历史记忆的漫漫长夜。具体从三个维度予以回答:其一,归纳新时期文学中历史记忆小说在不同阶段的书写特点;其二,分析历史记忆小说叙事在不同阶段发生流变的影响因素;其三,考察这些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和制约历史记忆小说的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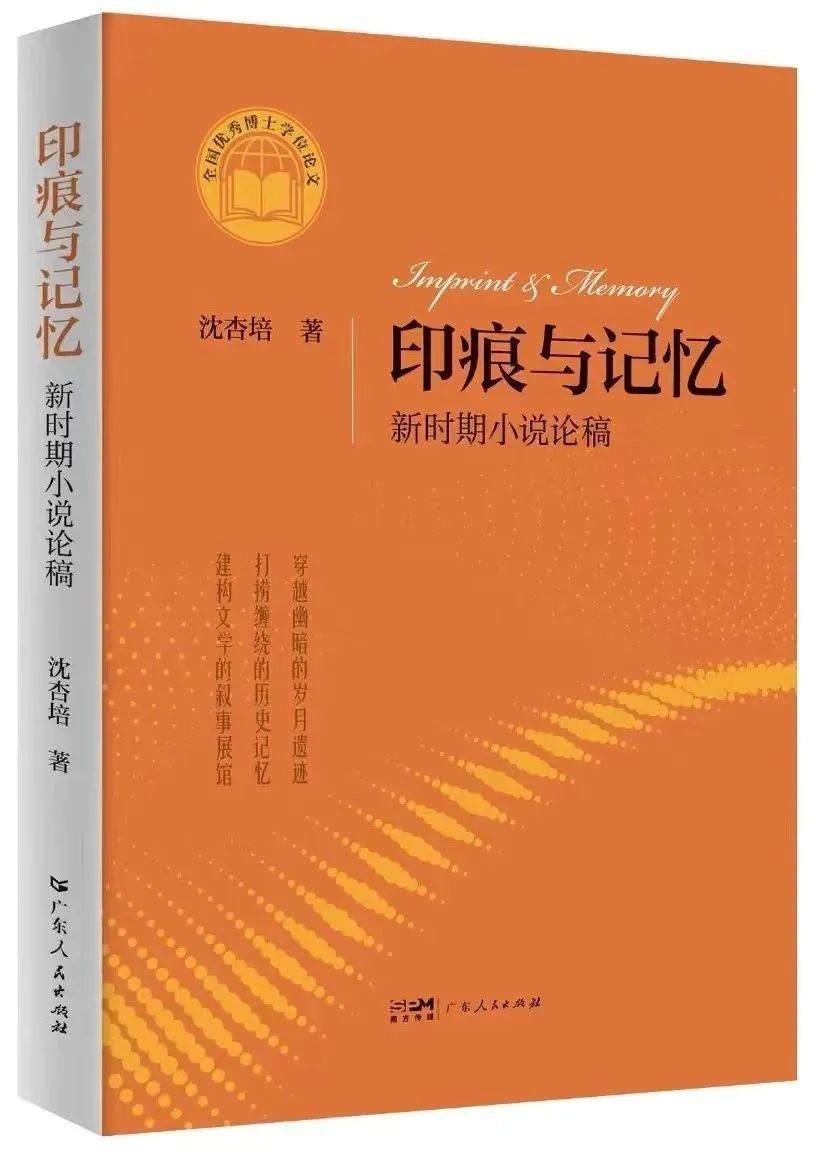
《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论稿》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发生学与变迁史的角度,将新时期小说中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记忆的小说铺展整合,梳理出不同时期小说叙述的阶段特征及流变形态。沈杏培以敏锐的时代感把脉新时期文学,准确捕捉思想转型时期的重要历史时刻,选择1985年和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为阶段区隔点,前者是“文学向内转”“人的主体性”讨论的重要节点,后者标志着文学生态发展多元化趋势的出现,以此将新时期文学分为三个阶段,论述各阶段时代语境下的文学特征,以及代表性文学思潮和典型文本,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新时期历史记忆小说的书写方式,总体呈现出从政治规约到主体自觉的文学转型,最后在多元化语境中逐步回归到主体自由心灵的审美中。
在梳理新时期历史记忆小说整体概貌的基础上,第二章从叙事学的视角归纳历史记忆小说的叙事方法。方法论的介入,实际上是借助热奈特之镜,以叙事作为考察基点,建构出新时期历史记忆小说的文学展馆。沈杏培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对四十余年的文学盛宴进行有效归类,在叙事视角的整合中发现了动物视角、儿童视角,揭示现有文学谱系的部分创作共性。此外,沈杏培通过对小说群像的不断提纯和简化,剥离出“群众”概念的变迁史。“群众”作为舶来词,自近现代绵延至今,在新时期文学中以人物形象、主题话语、某类母题的形式不断重现,将其作为承载和透视这四十年历史记忆叙事的重要参考,可谓以小见大。与聚焦小说文本、归纳叙事方法不同的是,“群众”的话语变迁史,更是验证研究者思维预期和方法效用的重要凭证,这表明“笔者试图探寻作为一种持续性书写的历史叙事(1966-1976年)发展到这一时期呈现出何种特征和形态”[1]的理想信念得以落实。第三章在方法论的维度上继续着力,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史视角对其展开研究,探索并总结出历史记忆小说叙事受政治文化、消费文化、代际文化和历史观等诸多因素影响。
第四章将海外华语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叙事予以纳入,由此达到双重效果。一方面,通过建构历史记忆小说叙事的世界视野,拓宽写作样本的地理区域和文化范畴,更为全面地观照历史记忆的叙事地貌;另一方面,以华语语系的文学书写为镜,反观本土书写的既有症候。终章基于前文高度凝练出的影响历史记忆小说叙事的因素,以高度的历史关怀诊断历史记忆的叙事困境,将社会历史与文化现象的关联掣肘问题推向纵深。在准确定位叙事困境之余,《论稿》进一步给出建设性建议,提出小说书写的可能性向度,最终回归本论题的研究初衷,热切呼唤建构叙事伦理。
纵览《论稿》的章节分布和论述层次,可以看到其内在阐述逻辑是相当自觉的。在沈杏培的论述中,他将八十年代中期重要的文学事件纳入考量,兼顾新时期以来的政治语境变迁以及市场经济涌入后的社会语境急转,勾勒出小说叙事背后更为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尊重文学思潮和文学表述在各个时期的转型和调适,对文学史演进中不同流派的历史记忆小说进行归纳,对作者的创作方式予以剖析,选取典型文本进行阐释,由此按照时代演进和创作特征建构起历史记忆小说的作品群像。概言之,沈杏培在其论述中建构出“历史现实——文学思潮、文学转型——作家特定语境下的历史记忆小说创作——作品群像”的论题分析链。基于此,当代文学叙事展馆中的小说不再以松散杂乱的繁复形态出现,而是在每部作品闪耀的同时,也能循着分析链理清其来路,有知一隅而观全局的整体俯瞰之感。直观可见的是,《论稿》涉及的当代小说文本近两百篇,沈杏培以高度凝练的思维总结概括出同类型小说的新质。以主流文学史所认可的小说思潮为例,在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到新写实小说的演变序列中,展览小说成果的丰硕。从历史记忆小说书写的维度来看,每一思潮之下的小说文本又蕴藉着时代背景的更迭和作家创作心理的转变。传统秩序的解体、既有价值的失序,逐步引发小说创作寓言化、心理化、象征化的特征转向。
基于翔实的小说谱系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论稿》可谓特征鲜明:从时间发展的维度上可谓全,从叙事特征上可谓深,从文本取样上可谓广,从影响要素的归纳上可谓博。《论稿》本身作为完成度相当高的研究著作,以民族关怀始,以伦理建构终,实现了论著自身的论述回归。
二
求疵的自觉:政治/文学的震荡与创作/批评的对话
历史记忆小说叙事研究,看似是指向当代文学中的某一特定小说题材,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层面的质询和追问:历史记忆在小说中如何被叙述?历史记忆为何被作家如此叙述?作家叙述的历史记忆又该如何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动态关联、当代作家的心灵史和精神站位、文学史书写和文学评价体系等复杂命题。
《论稿》的研究思路折射出沈杏培的研究史观,即还原文学发生的原始场域,尊重既有的政治史实,在此背景下勘探文学的震颤方式。以此反观《论稿》,可以管窥出沈杏培在历史记忆研究背后更为深刻的文史思考。对他来说,小说叙事的阶段归纳和创作特色的发掘仅仅是研究起点,他所致力的是穿透文学作品连缀而成的历史地表,尝试从源头勘探限制或塑造文学发展的临近场域,进而达到对于文学演进的律动把握。这种把握的本质,是追问文学与历史演进关系的一种外显。换言之,沈杏培所关切的是,在文学紧贴政治之际,文学如何随着政治震荡,又因受到何种因素嵌入而异化?更为低喃的疑问是,文学多大程度上能够葆有独立表达的权力?
这一追问,实际上将此论题的对话主体标记出来,即批评者和小说创作者。二者的关系颇为缠绕,就批评研究而言,批评者暂居“审视者”的位置,借助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追踪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心灵轨迹,暂时得以理直气壮地对作者提出批评建议,并在历史逻辑和宏大叙事上取得自我确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然而,从文学批评的发展而言,二者又处于共生状态。沈杏培在《论稿》前言中指出,文学自主性受外界因素影响而数经波折,经历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去政治化”热潮,又迎来了21世纪初“再政治化”的学界号召,这一号召不仅是对作家的期待,“呼吁作家以开放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自觉进行文学实践,参与文学场域的重建,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到民族精神文化遗产的反思、民族集体记忆重构的实践中去”[2],也是对于批评者的引导。此时,批评者和创作者在文学场域中形成了双声部,彼此交荡着对于历史记忆的个人私语。
诚然,批评者的文学使命任重道远,如果以序列的方式标记出批评者的文学坐标,在时序上处于历史现实与作家之后,在时代敏锐意识上则必然需要超前,正如鲁迅所言:“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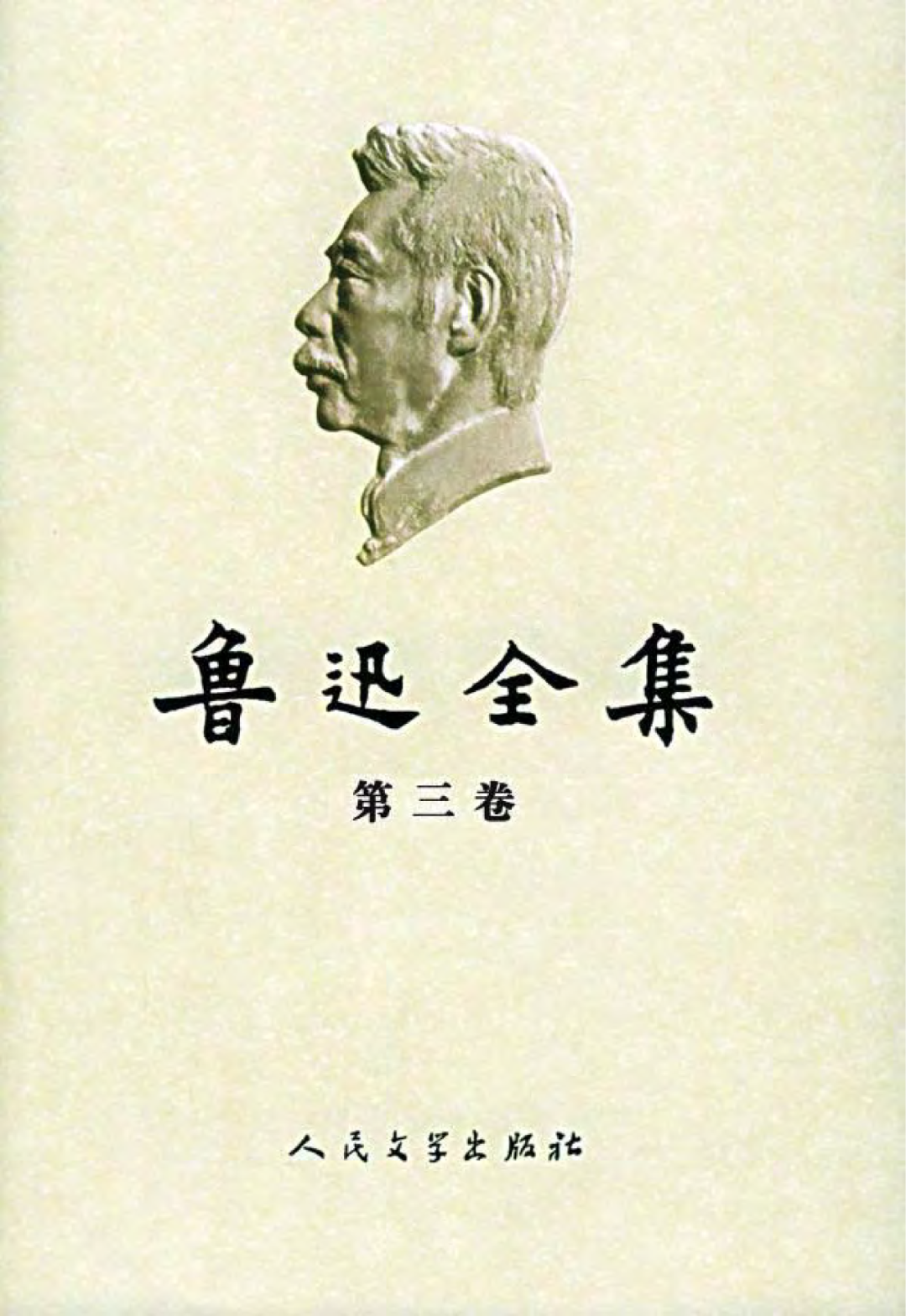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也就预示着批评实践的主体对象及研究视角多元而复杂。沈杏培的学术批评实践,始终以观察者的姿态高举着自己的文学检录仪,从各个角度寻觅最佳探讨位置,然后将镜头逐步拉开,从见微知著到俯瞰全局,以深刨的姿态对时代命题予以回应,以批评者的姿态编织出批评视野中创作者与现实的关联,以反思的姿态追问诸多问题的形成及根柢。
然而,由于批评本身并不具有确定的范式,批评审美和批评风格在众多批评家之间也标尺迥异,那么,何种批评才是有效的?这是沈杏培一直思索的问题。他认可别林斯基所说的“批判理性”,并且谨慎使用写作的权力:“倘若我们不想让写作沦为一种任性而野蛮的权力,不让它沦为审美名义下的道德放纵或商业动机驱动下的文化犯罪,那么,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在面对作家的新人时就必须‘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存在一点的不信任’,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执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一种‘高明的怀疑态度’。”[4]因此,他警惕“化繁为简”式的义理叠加、“邻猫生子”式的伪问题、“砍头割脚”式的阉割批评模式、“求全责备”式的错位标尺判断。[5]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引发了他的批评共鸣,其批评态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6]中可见一斑,着重批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因研究者的史料缺失及研究力度缺乏,所造成的松散关联、虚假关联和庸俗关联。他曾明确提出自己的批评主张,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正义”与“及物”的内在属性: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在“寻美”,更是一种敢于冒犯、体现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求疵”过程,是散发着知识分子正义的“及物”活动,是批评者“不低于”批评对象的对话与“问诊”。[7]
沈杏培的“求疵”追求并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更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予以落实。在此部《论稿》中,他以研究者的身份主动介入并追溯到文学创作现场,综合考察时代语境、文学转型等历史情境,这也是对影响创作者的可能因素的一次集中扫描。在做好此种准备工作之后,他以同情之理解,将目光聚焦回创作者,以代际差异分析出生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作家群。由于同一代际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创伤,他们的审美方式和历史认知、叙事方式之间存在共通之处。然而,不同代际作家距离历史现场情况有所不同,对于这段历史记忆的认知呈现出亲历与远观的梯度人生体验,基于历史经验的差异,衍化出亲历者、旁观者和想象者的角色区别,进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以不同的寓言方式将其变形,纳入文学创作之中。幻想、夸张、变形、感性等创作方式背后蕴藉着作者的狂欢和补偿心理,同时也折射出不同人生阅历和人生体验熔铸而成的作家历史观。
沈杏培之所以关切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不仅是文学研究中需要知人论世,更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学创作者的笔墨将会承载今后历史记忆的绵延,那么知识分子肩负的并不仅仅是文学盛宴的繁华使命,也包含着历史真实、民族记忆的宝贵留存。《论稿》中提出:“作家是如何处理历史记忆叙事,作家的历史观念如何影响历史记忆生产,意识形态的规约、作为治疗历史创伤或契合大众消费的时代要求是如何制约、改变、塑造作家的历史记忆叙事,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究。”[8]作家创作原本具有私人性,但在作品出版面世乃至进入文学史后,小说本身兼具时代印记与作家意识的双重标签。虽然在“作者已死”的观念中,读者争夺到宽裕的解读空间,然而沈杏培关注的是,作品作为作者、读者与时代的连接物,具有见证历史、抵制遗忘和建构公共记忆的重要历史介入特征,因此,当民族之殇发生后,作为创写公共性文学的作者,是否可以存有对于民族历史的敬畏和关切?当文学创作被众声喧哗的社会背景稀释、异化、削弱,文学是否可以接续起八十年代的文统?在并不强求文以载道的年代,作者是否可以产生抵制历史记忆遗忘的自觉?
历史记忆小说研究,与其说是呈献给文学史的一部力作,不如说是给作家们创造的回溯民族记忆创作谱系的契机。该部《论稿》试图达到的是,唤起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以文以载道的创作精神肩负起表达、反思并延续这段历史记忆的人文使命。
三
及物的延伸:民族记忆的“类经验”与叙事伦理建构
在《论稿》自序中,沈杏培以极其真诚的态度坦诚研究缘起。作为出生于八十年代的新时期青年,在探知家族历史的过程中,他逐步触摸到父辈隐秘的精神伤痛,以文学的同理之心体悟近在眼前却不在场的历史,以思忖的姿态尝试在这蕴含代际阵痛的历史狭道中,窥出照亮未来的星点光亮。这种文学自觉的努力,某种程度上是以幸存者的历史余温,延续、重塑历史记忆的废墟,擦拭蒙尘的心灵灰垢,以文学之呼吸重启生命体验的缺失或离场。
如果将目光透过这份早期关切的议题,可以看到,沈杏培的研究志趣背后,镌刻的是大写的“人”。表面上,他在新著中梳理文学脉络中与人的生存相关联的质素,进而追问人的生命印记是以何种形态变化、形塑,继而嵌入文学之中。实际上,他所探索的内核是,经过某段历史冲刷的亲历者和后来者,他们的生活被镌刻下意料之外的痕迹,甚至终其一生都无法自愈,那么这样的一批人又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对于历史记忆书写方式的考察,其深层追寻是在观察被历史打下烙印的人,如何自我面对、表述并纾解构成自身生命的异质。沈杏培以批评家的姿态殚精竭虑,为文学场域中出现的人操心,从人物原型到作者本身,都构成了他关切的人文主体。
可以说,沈杏培的学术肇始于有情的文学关怀,他以铁肩担道义的历史责任感抵达文学研究和学术批评的现场。正如他所袒露的:“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本书既是执着于追问当代作家如何建构历史记忆叙事这一文学命题,同时,又是在深层意义以及价值探寻上追问当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如何面对自己民族的精神苦难、如何中断或修复这段历史带来的民族创伤记忆和创伤情感、如何阐释与处理这一20世纪中国学人所独有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9]这种努力可以视作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研究上的共同追寻,也呼应了同时期学者观察到的一种现象,一种努力的存在,“试图把无数人的幸存体验转化为积极的历史遗产”。[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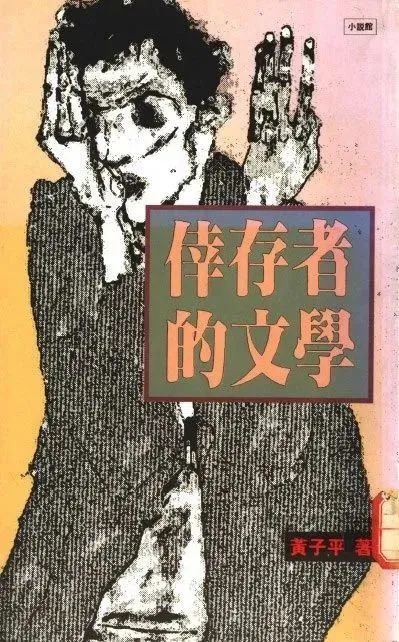
《幸存者的文学》,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
基于民族共同经验的个体书写,如何上升成为人类的“类经验”,这是历史记忆题材创作想要走出中国文学气象所面临的问题。九十年代中国作家创作多样化后,如何处理集体经验与个体经验、如何将丰富驳杂的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整体性的文化反思与文学叙事,这是沈杏培所关切的问题。[11]这既是民族历史的自我反刍,也是在历史记忆延长线上的自我体认,更是检视是否消化和走出既有历史阴霾的现存气量。由于历史叙述与文学史建构的方式蕴含着话语权力的渗透与操纵,因此,所有介入历史叙述生成的主体和质素均对历史记忆的表达和呈现产生影响。基于此,在沈杏培的历史观察中,他总是有意识地给自己按下历史的暂停键,留有历史思忖的空隙。虽然文学发展有其时间上的先后性,但线性时间观或进化时间观背后所涵纳的是等级化的时间及新的话语秩序,他认为:“当进化论的认识观投影到时间的认识与历史的观照上时,时间即变得不再纯粹。这种‘时间神话’的显性标志便是文学史与批评话语中有关‘新纪元’‘新时期’等语汇的诞生。这些语汇本质上内含的是社会形态、权力主体及其话语规范的变迁。”[12]新时期文学的概念指向中蕴含着对旧时期文学的颠覆,同时也通过区别于旧有文学来获得自身的主体确立。然而,时间的更迭并不代表精神层面的进化,相反的是,概念更迭的速度之快,反而彰显出与既有历史匆忙切割的恐惧和无措,在此意义上,对于历史记忆的沉思,仍有其存续的价值。
在新时期文学研究汗牛充栋的当下,沈杏培的新著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史意义。这部《论稿》是基于文学研究痛点而产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同时也是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回避重大文学命题的质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期待和召唤已经存在:“从‘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角度,人们曾产生一种期待,期待总会有一两枝‘如椽大笔’出现,以新鲜而激动人心的形式,写出饱经忧患的民族的大恐惧和大希望,来震撼我们疲惫麻木懦弱的心灵。”[13]然而,至今尚未有全面而深刻的文学研究对这段历史记忆展开论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沈杏培的新著可谓是迟来的文学补偿。然而,这部书稿的出版也数度历经坎坷,曾在无望出版之余,部分章节以单篇文章的形式见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重要期刊,以只言片语的碎片形式,通过阐述某个核心问题发出反思时代的声音。现今书稿得以结集出版,算是给单篇漂泊的文章一份归属。形式可谓内容的另一种呈现,如今呈于诸君眼前的书稿,章节分布似乎未遵循均衡审美的原则,究其原因,也是书稿的纯化要求所致。“跛脚”的章节形式已然昭示出探讨这一历史记忆的曲折,其中艰辛恐怕只有作者本人才能穷尽。尽管如此,面对早期投注心血的议题,沈杏培依然有所期待:“时至今日,文学知识分子对这段历史的叙事热情并未减退,只是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文学远未达到壮阔、伟大的境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我总在想,既是诗家之幸和文学之幸,扛鼎之作和旷世大作为何还是缺席?这本书包含了我对这个问题粗浅的追问。我坚信,历史歧途一定能够催生出文字的盛宴和文学的盛世。”[14]
注释
[1]沈杏培:《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第4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2][8]沈杏培:《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第6、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3]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5]沈杏培:《自序:文学批评的“理性”和“及物”》,《私想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现象观察》,第4、4-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6]沈杏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
[7]沈杏培:《正义与及物——关于文学批评何为及当前困境的思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9][11]沈杏培:《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第3、1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10][13]黄子平:《自序》,《幸存者的文学》,第5、6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12]沈杏培:《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第2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14]沈杏培:《自序》,《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第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