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沈杏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江苏省首届青年社科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南京师范大学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人选、南京师范大学中青年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八十余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出版专著《私想文学》《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理性与抒情》等四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三项。荣获江苏省社科成果优秀奖二等奖、《小说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六届江苏文学评论奖一等奖、第二届江苏紫金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第三及第四届江苏文学评论奖二等奖、首届江苏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紫金山文学评论奖、金陵文学大奖、江苏省文艺大奖·首届文艺评论奖等。
困惑与自由:我的学术心迹
内容提要:寻觅一种理想的职业和良好的生活是我一直没有泯灭的内心渴求。我在困惑中不断选择、放弃、再选择,经过多种职业的历练,我把学术当作自己的志业。在学术上我向来抱着一种兼容并蓄的心态,这种“兼容并蓄”表现为对不同研究方法的好奇,对不同学术人的尊重,对各种学术命题的兴趣。学术的功能和意义对我来说意味着,把学术研究当作一种兴趣来珍视,把读书写作当作一种知识补给和自我修行,把文章学术当作通往现实世界和历史现场的一种介质。积极倾心学术的同时也警惕个体成为学术之奴,永远捍卫心灵的快乐和自由是我作为学术人的底线。
关键词:学术;困惑;选择;激情;自由
2002年我大学毕业,随后通过省委组织部选调生选拔制度,成为家乡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科的一名公务员。作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年不到,我便厌倦了这种程式化的生活,决心离开这份在很多人看来“非常体面”“很有前途”的岗位。翌年我便顺利考回南京读研,兴致勃勃重回心心念念的大学校园。三年读研期间,我大多数时间泡在图书馆,热情地阅读和思考,不知天高地厚地撰写并发表了若干论文,学生时代各种大奖小奖皆有斩获。但2006年硕士毕业时我并没有继续考博,而是选择了留校做行政,原因很简单,当时年近二十五六岁,我只想找份工作赶紧养活自己,减轻父母的负担。说实话,在货真价实的工资和岗位面前,当时我对于即将告别的读书生活并没有太多不舍。然后,我开始了近六年的高校行政生涯,这其中有三年在职读博。读博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始于厌倦继而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因为留校工作后的第二年,我又开始不满于这种琐碎机械的坐班工作,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够自由的生活状态,于是,留校后的第三个年头开始在职读博。在职读博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既要把主业工作做好,又要挤时间完成博士期间的学业。人的精力就那么多,哪块都不能马虎潦草,要按时顺利拿到学位,其难度可想而知。身边有很多在职读博的朋友,常常需要疲惫地应对工作和读博这两极要务,结果却一样落不到实处,最后在仓皇和焦虑中不得不选择延迟毕业或放弃读博。由于专业基础比较好,自己内心尚且喜欢科研,加上导师的帮助和自己自觉而勤奋地探索,我在博士论文选题、论文发表等环节很快顺利推进,经过很多的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学业的苦熬,终于在第三年按时毕业。我没有延迟毕业更没有放弃,因为读博是我摆脱当时厌倦状态的重要途径,读博是我解决职业发展困惑通往我渴望自由状态的为数不多的通道。2011年我顺利从行政岗位转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研室,成为一名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青年教师。

沈杏培
回头看这二十年走过的路,不短也不长,但我自己却清晰地知道,对于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我一直在调整,一直在寻找,我不愿意随便落在某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生活轨道里,然后按部就班地生活和度日,我不想做那种能够得到定时投喂却没有丝毫自由的笼中鸟。我一直在寻觅一种理想的职业和良好的生活。因而,我不断地尝试,不断地选择,又不断地放弃然后再选择。经过这些必要的折腾过程,我渐渐清晰地知道,对于我来说,中学教师、公务员和大学行政都不是我理想的工种,做个简单的知识人,读读书,教教课,写写文章应该是我比较理想的角色选择。因为,这样的工作,至少看上去自由而优雅,纯粹而自足。我很感激二三十岁时自己内心的那种倔强和“不断折腾”的蛮劲。我从小就属于乖巧听话的“好孩子”,对父母和老师的话言听计从,但成年后的职业选择我似乎只愿意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何为理想的工作,何谓理想的生活,我不愿意简单接受别人的定义和建议。我相信大学的学术生活是一种相对比较理想,是我能适应也会喜欢的生活。然后,我便一头扎进这种学术生活中,阅读、思考、写作、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拿项目、评奖、评职称、评荣誉称号,这些进展都还算顺利,这种张弛有度较为顺利的状态也让我不断确证着学术生活是我的理想生活这种信条。
中国自古就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俗语。这句话用来描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能适用: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常常是描述性的定性研究,不同研究成果其质量固然有高下优劣之分,但不同研究的区别大多时候表现为研究视角、方法或范式上的差异性,很难说在结论和性质上一定就有谁高谁低谁错谁对之分。比如你研究传统文学,我研究网络文学,你研究鲁迅前期思想,我研究鲁迅后期思想,你用版本学研究《狂人日记》,我用原型学研究它,你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开端,我认为这种现代性滥觞于晚清——这些差异更多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或者研究结论上的差异,没有对与错之分,更不应有谁可以取代谁。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正是由于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有着这种清晰的认知,我在学术上向来抱着一种兼容并蓄的心态,这种“兼容并蓄”表现为对不同研究方法的好奇,对不同学术人的尊重,对各种学术命题的兴趣。从学术心态来说,我一直以“学徒”自居,不是谦辞和话术,而是内心的一种真实想法。给研究生上课时,我常常把本专业学术研究中那些颇有特色很有启示的研究成果如数家珍地介绍给学生们,以至他们很是惊讶于我对学术史和学术前沿的熟悉程度。这些研究中不仅有学科大佬和学术名流,也有很多是在读博士或是学术“青椒”。因为我敬重每一个写得好文章的同行,我非常留意那些有真正创新的专业研究成果。从学术研究的范畴来看,我不愿意死守一块,然后深耕细作,经年努力之后成为某个领域的所谓行家。我希望我的研究广阔多元,尽可能涉猎广阔的文学和广阔的现实与历史,尽可能尝试更多的知识谱系和学术命题,尽可能在学术兴趣的驱动下在无限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开疆辟土。我不愿在一个狭小的学术领地里急吼吼要留下所谓自我的学术脸谱,我宁愿保持一种自由生长态势和快乐勘探的姿态,哪怕这种状态只是在一种孤独和无名之中进行。在当下过多强调代表作和属己学术领地的评价体系下,我其实不太介意别人的评价——在一个异常喧嚣甚至极度拥挤的巨大学术广场里,有那么多声音那么多面孔,为什么一定要挤到前台在那狭窄的印匣里留下自己的手印或脸模?把学术研究当作一种兴趣来珍视,把读书写作当作一种知识补给和自我修行,把文章学术当作通往现实世界和历史现场的一种介质,这样的学术状态岂不更舒适更有意思一些?概而言之,我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意思:我甘愿做一个学术无名者,在广袤的学术空间里,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视点,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或是安静自在四处漫游。纸上写就辉煌,那是后世人的评论,内心自在快乐,这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我从不想让学术成为生命的全部,只希望它是部分,在浩瀚的世界和五彩的生活里,有太多值得投入的东西。如果学术成为我们生命里的束缚和负担,成为一种异化性力量,我想说,我们不能成为学术之奴,要永远捍卫心灵的快乐和自由。
近十几年,我的学术大致沿着这样几个方向展开:第一块的研究,围绕博士论文形成的学术思考继续深化和推进。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关注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记忆问题,近些年经过打磨和完善,这部书稿以《废墟与盛宴: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于近期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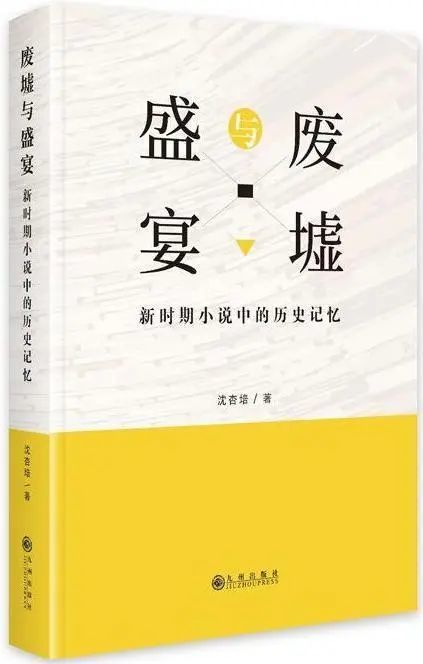
《废墟与盛宴: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
这部小书试图从发生学和变迁史的角度全面梳理新时期四十余年来小说中的历史记忆,力图以“史”的眼光全面梳理和深入阐释历史记忆及其叙事在不同阶段、不同创作主体、不同社会语境下生成、变异的动因及其昭示的文学史价值,也试图在世界文学坐标视野下考察中国历史记忆小说的优势和局限。本来我是接着这一方向继续做海外华语作家文学中的历史记忆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只能暂搁这一研究。第二块的研究,是在原来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然延伸。我将研究范畴聚焦到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诸多重要文学现象的考察上,主要关注新世纪小说的现实性、介入性和公共性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介入性与公共性研究”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时等级被评为“优秀”。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成果已结集为《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三块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学资源与经典作家、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这块研究主要从本土资源、域外资源两大角度考察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风格、与所接受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这些资源如何塑造、影响或决定作家文学风格的生成。通过对王蒙、毕飞宇、张承志等个案和众多文学现象的分析,找寻阅读资源、地域资源、本土资源、国外资源如何影响和塑造作家的写作风格和叙事技艺,从“阅读史-接受史-写作史”的三维考察视野,确认了域外艺术、文化资源与中国当代作家艺术视野、文学叙事和思想认知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了接受主体在接受和化用各种资源时的方法、策略和特征,从影响资源的角度厘清了当代文学思潮和文学风格生成的原因。第四块的研究,主要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反思,发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正义与及物——关于文学批评何为及当前困境的思考》《文坛需要这样的“求疵者”》《普实克和夏志清的鲁迅研究及其方法论反思》等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有的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并获得一些学术荣誉。这四个方向是我近些年比较关注的内容,进入这些学术领地的方式,一种是文学批评,另一种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特点是自由而凌厉,问题意识和现场感强,学术研究则更加注重学理和表述规范。我近些年的学术实践,在这两方面都倾力颇多。
中年常常是容易发生“变法”的时期。当学术激情渐褪,学术靠什么维持和推进?稻粱谋、工作惯性、职业本能,还是更为宏大的学术壮志?近几年,我总感觉我的状态在悄然发生变化,对学术渐渐滋生了一些困惑和厌倦。一是学术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疑问就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样,经常盘旋在我的心头,而又无法获得一个确切的答案;二是我明显感觉,随着年岁渐长,我的专业激情明显在减弱。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我一直没有清晰找寻到所谓意义。而我自己的学术激情却一点点在流失,不再像从业之初,什么问题都想去思考,脑袋里总是有很多头脑风暴,由此生发出绵延不断的阐释激情。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名篇中,提出一个经典的命题:以学术为业是一种疯狂的冒险活动。

《以学术为业》(节选),《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他说的“冒险”,不单是指德国在任命大学教师时常常要受制于集体意愿这种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也不仅仅指年轻学术人需要面临教师和学者“双重任务”,更主要的是学术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化程度极高的职业需要众多重要品质。在这些品质中,“激情”是韦伯极为看重的一种品质。韦伯借柏拉图的《理想国》把“激情”视为一种有意识地发现科学知识的伟大工具。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激情”,即便内心真诚、知识渊博,也不能使一个问题产生科学结果。由此,韦伯提出“学术倦怠”的普遍问题:一个许可自己进入专业“共同体”,从事永无止境的研究,并且其研究成果注定要过时,那么所期望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全新的思考[1]。韦伯甚至引申出另一个更为宏大的追问:在人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职业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韦伯提出这个问题比他如何回应这个问题更为重要。这个提问,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时是如此令我困惑和不安。从大的语境来看,人文学科的边缘性处境和人文知识分子言说在当下受到的重重限制,已经决定了文学研究只能在学科谱系和知识话语层面不痛不痒地进行,学术的思想性、批判性、现实性,以及起底历史真相、言说时代症候、自由表达知识分子爱憎和立场的学术维度,大概是难以存在的。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能蛰伏于一己专业,小心翼翼地规避各种话语禁忌,只能张扬所谓岗位意识而收缩广场意识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学术人所置身的学术环境已很严峻这一现实。这种语境决定了学术的限度,影响了学术人的精神面貌。从个体角度来看,我喜欢的是那种有质地、有张力的学术研究,我喜欢和当代生活相连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我喜欢独立而批判地进行学术研究。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强行关联研究、无用的善和盈余的恶、计划生育叙事、批评的及物与正义等专题研究中,都表达了一种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爱憎倾向,这些研究不是简单的知识叙事,而是包含了对一些重大命题的批判性思考。美国理论家菲尔斯基在新作《批判的限度》里,将批判称作“一种如此有魅力的思维模式”,并将批判描述为一种怀疑的阐释学,他认为,“批判意味着睿智的思想实践、思维的独立自主。同样,谁拒绝批判,谁就会陷入自满、轻信和保守的泥潭。”[2]当菲尔斯基所说的批判作为一种“适当的思维冒险”难以为继时,我们还有捍卫我们牢骚满腹和善意批判的权利吗?
鲍曼在最近的一本访谈著作中,这样形容消费主义语境下个体悲剧性的生存状态。他说:“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可矛盾的是,这种强迫——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3]

《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鲍曼对“消费社会”的这种观点,如果挪移到学术人和学术生活中一样非常准确。没有谁会否认,当下是一个学术消费主义的时代。文科被“科学-工程”式的学术评价体系笼罩,人文学科需要按照既定评价条文源源不断地量化生产成果,否则,便成为出局者。学术人的学术实际上异化为“把自己变成一件人们想要的、可以营销的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带来职称、名声、货币和好的生活。一种已经固化的学术制度早已让人文学科的研究丧失了该有的雍容、自由和空间,转而在一种急功近利得近乎凶神恶煞的氛围中试图把每个人文学者驯化得同样高产又高效。于是,我们必须变成那种“理想的”学术人,才算是成功的学术人——一种耗尽可爱的生命写着无聊无趣文字的那些人。鲍曼在这篇访谈中的另外一句话深深击中了我:“这种义务的‘必须’感,和人们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许多人也因此发起了反叛。”[4]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这一刻甚至近几年,我深知内心的这种“反叛感”是何其强烈。我知道我们消耗青春、时间和精力所用心经营的这些所谓学术研究,除了带给我们物质性的生活和那些可有可无的荣誉之外,大多数注定很快成为历史的多余物和遗忘物。人生何其虚空!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一切都指向那宿命的无意义。那么,认清了这些所谓真相或残酷,个体又能怎么样?事实上,除了规规矩矩按部就班,老老实实回到既有轨道,几乎没有太多选择。难道因为这种不满,我们会放弃多年的行业经营而重新开辟第二条人生通道,重新在其他选择里重建生之自由?在这些困惑、厌倦和反叛之余,其实我依然很努力地在阅读、思考和写作,在搜集史料,在构思一个又一个论题,在规划着下一阶段的职业目标。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意识到了很多问题却未必能解决这些问题,感觉到了某种痛苦却未必有医治这种痛苦的良药。我依然困惑着,我依然前行着,我依然向往着生的自由。
该说句结束语了。面对学术,我仍然会庄严己心;面对人生,我遵从得舍从缘。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自由在高处”。为了这最好的自由,最真的自由,我会继续向着高处进发。
注 释
[1][德]韦伯:《学术贵族与政治饭碗》,刘富胜、李君华译,第1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2][美]芮塔·菲尔斯基:《批判的限度》,但汉松译,第6、1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3][4][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第104、10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