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 简 介
王尧,苏州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兼及文学创作。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当代散文史》《“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莫言王尧对话录》《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历史·文本·方法》《王尧文学评论选》等,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丛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文革文学大系》等,另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日常的弦歌》等,先后在《读书》《南方周末》《收获》《钟山》《雨花》《上海文学》等开设散文专栏,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等。
从散文的字里行间走过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作者散文写作的历程,体现了作者关于散文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情感存在方式的主张,并提出了作者对什么是好散文的理解。
关键词:散文;人生;知识分子;文体
人的一生大抵是一篇散文,中间或许有诗有剧有小说。我所有的写作,便是从“散文”的字里行间走过的印记。
我现在能够记起的公开发表的文字,大概是 1981 年上半年刊登在《辽宁青年》等刊物上的短章,所谓的“散文诗”,印象中是感慨人生的。同学们看到我有邮政局的汇款单便起哄,我取了钱,买了包子,若干同学边吃包子边哼起歌曲,这是我在东台县城一年留下的最开心的时光之一。后来我有些后悔,应该留几毛钱,买一串香蕉带回去给妈妈。妈妈那时患肾脏疾病,喝了太多的汤药。东台中学附近便是体育场,我有时会从宿舍到那里跑步,好几年前,我曾和村上的小伙伴行船几十里,到这里割草。后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文字,是从汤药和青草的露珠还有码头的青苔上生长出来的。这些元素影响了我文字的调性,温暖、忧伤、凄凉和透明长久地在我的字里行间弥漫。

大学时期的王尧
尽管我写出了或许以后无法再写出的句子“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但我知道坐在码头上我的视野是有限的。在河对岸的房子只有几幢时,我能够远眺到的,也只是一片田野尽头的公路,公路南面的河流也目及不到。直到我看见汽车从公路上驶过,直到我坐上其中一辆车去县城,我才知道自己的想象也是有限的,甚至是荒唐的。没有生活和知识支撑的想象总是有限的。我背着一个木箱,坐上了汽车,一路是颠簸还是自己内心起伏,我终于到了县城汽车站,再从那里坐上了去苏州的汽车,早晨出发的,到了八圩已是下午。轮渡启航时,我回头看了看江北。人生的起承转合,成了散文永远的结构。
在后来的文字中,我多次叙述过第一次到苏州的印象。相关文字,我几乎没有满意的。我知道,只有当我和苏州融为一体时,我才能写出我的苏州和苏州中的我。检索自己的文字,发现几本散文集里都没有独立写苏州的散文。我在苏州学习生活工作了四十余年,在这里发育了思想老化了筋骨,也在此地回望故乡,观察中国和世界。其实,我现在生活的苏州和之前生活过的东台,互为“故乡”和“他乡”。我没有见过镇上老屋的那个匾额,父亲说堂屋里挂着“三槐堂”。我丝毫不怀疑父亲少年时的记忆,我在个别方言和生活习俗上确证了父亲的说法。几年之前,在三槐堂宗亲聚会时,我在无数陌生的头发和脸庞上发现了共同特征。我不知道我的那位先祖是怎么跋涉到东台,再到时堰的。数百年以后,他的他乡成了我的家乡,我负笈江南后,他的第一故乡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错落的时空中生活。1983还是1984年,我在中国散文学会的刊物《散文世界》上发表了《脸谱》(五题),这是我正式写作散文的开始,其后近二十年间,我几乎没有再发过单篇散文。《脸谱》写故乡人物,2021年出版《时代与肖像》时,我收进了这组文章。1996年,人民出版社的方鸣先生知道我喜欢写作散文,说可以给我出版一本散文集,而且要做成毛边书。毛边书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我就收拢了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一些文字,结集成《把吴钩看了》。1998年出版的这本毛边书中的文字,有故乡记忆,有序跋,也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随感,其中《和孔乙己聊天》留下了我当时的思绪。虽然我也用一把裁纸刀裁自己的毛边书,但心思和精力在学术。这二十年间,念书,师从范培松先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从研究中国当代散文史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也做了很多文学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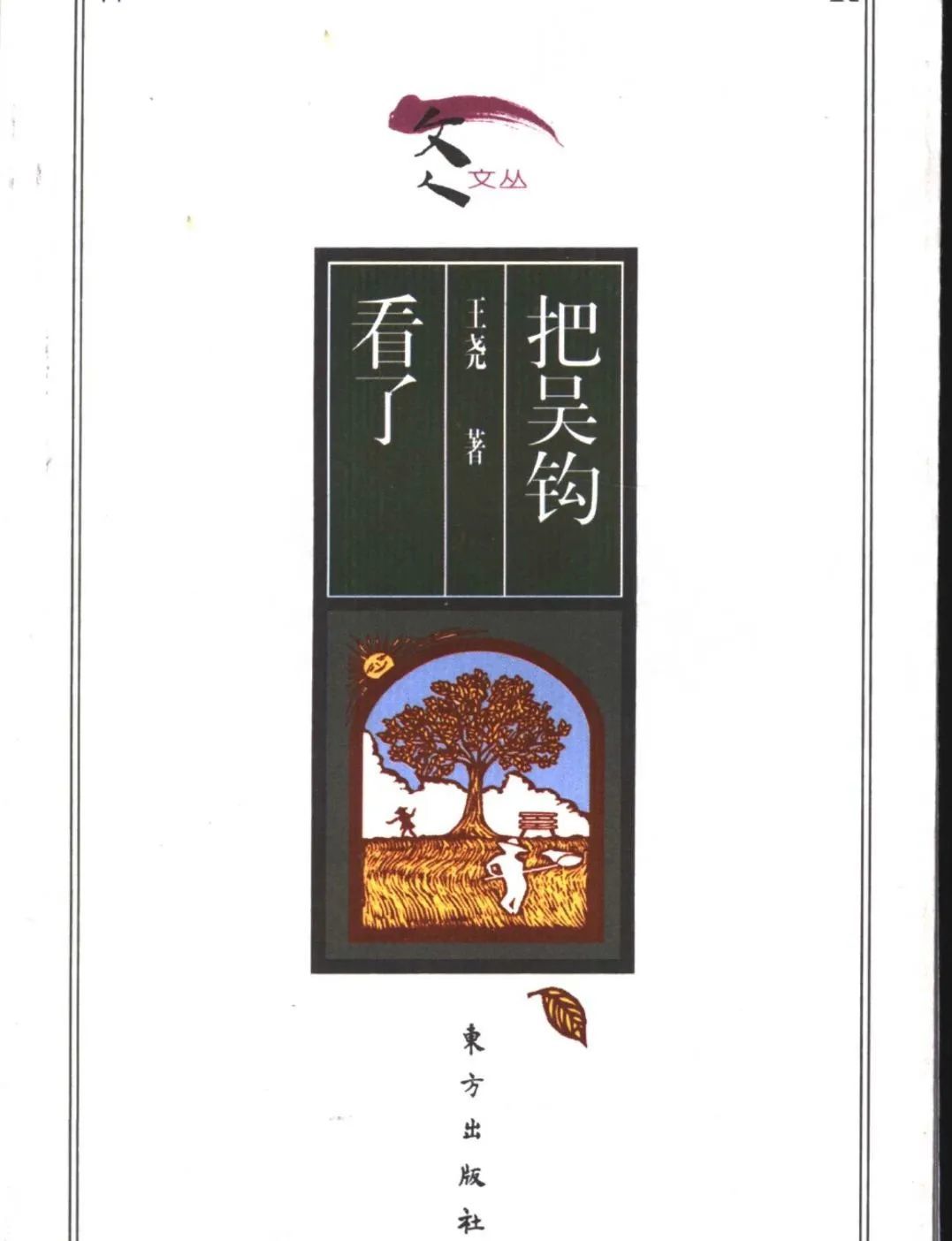
《把吴钩看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001年我和林建法先生策划了“小说家讲坛”,在和作家的互动中,那个遥远的作家梦又在内心活跃起来。“非典”的那一年,我应邀给《南方周末》开设了“纸上的知识分子”专栏。我从武汉坐火车去了咸宁向阳湖农场,在那里访问了几天。在潇潇春雨中,我和曾经下放在那里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场景中“相遇”了。我想以自己的方式,向那些崇高和卑微的知识分子致敬,我向往崇高但我也卑微。尽管这只是想象,但却是我以散文的方式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开始。我的学位论文是做“文革”时期文学的,在写作专栏时,我开始考虑能不能在学术之外,以小说和散文的形式呈现我关注的问题。《南方周末》专栏文章后结集为《脱去文化的外套》,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一年的专栏写作,让我筋疲力尽,我几乎是发誓以后不再写专栏了。但十几年以后,我又忘记自己写作专栏时的疲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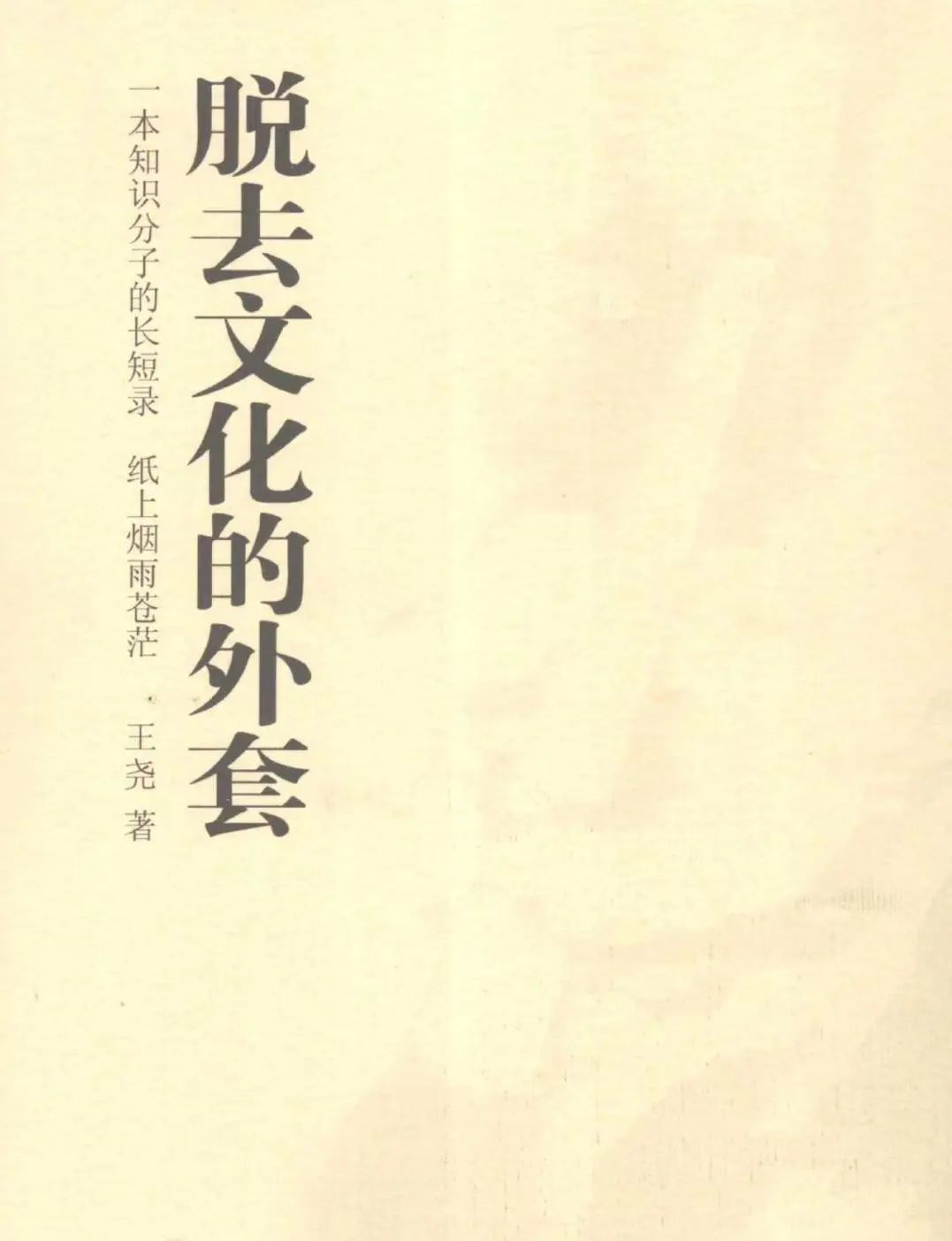
《脱去文化的外套》,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我青少年时期的寒冬大雪纷飞,那种寒冷的感觉让我现在也不寒而栗。初到苏州读书的几年,待放寒假时也会遭遇大雪。逐渐地,大雪小雪都成了一种企盼的风景,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2008年春节将至,一场大雪突如其来。我坐在书房里,透过北窗户,看到小区围墙上已经挂了久违的冰凌,遥远的记忆又复活了。一个寒假,我都在写作中,很快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交给华东师范大学的倪为国先生。2009年春天,我在台湾讲学时收到了两本《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说写作《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时,我看到了年轻的我向我走来。这个年轻的我,是八十年代中的我。我一直觉得八十年代对知识分子是如此重要。《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是我的思想史,也是我的思想方法。因为这本书,我一直知道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八十年代的血。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10年我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半年,这是再次生活在错落的时空之中。很多年来,我一直想有独处的机会,在卸下所有的社会工作负担后,我觉得一身轻松。到波士顿三个月后,我就瘦身三十斤,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飘逸,仿佛回到大学时代。我带了很多降压药,但几乎不吃药,血压就正常了。回国时,我大箱子里装的是因瘦身不能穿的过于宽大的衣服、储满英文论著扫描件的硬盘和多余的降压药。这个半年,让我有了一次清洁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可能。我并不崇洋媚外,但访学的经历让我知道了,我们既要在中国看世界,也要在世界看中国。出国前《读书》主编贾宝兰女士邀约我写文章,这就有了《读书》专栏“剑桥笔记”。我很少重读自己的文章,但经常会再读《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其中的一些文章,后来收进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出版的《纸上的知识分子》中。高秀芹女士建议我编一本散文选,我想起当年出版《脱去文化的外套》时最初使用的书名,就将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散文选命名为《纸上的知识分子》。

《纸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读书》“剑桥笔记”陆续发表后,《收获》程永新先生致电我,说了些肯定的话。我特别在意永新兄的意见,也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几年之前,我曾经在《收获》发过一篇散文《在台下聆听和张望》。永新兄要我考虑考虑,有没有在《收获》开设散文专栏的可能。我说想想,这一想就是五六年。记得是 2017年9月,永新兄电话我,问有没有想好,我说了两个选题,他选了写重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这个题材。这就有了2018年《收获》的专栏“沧海文心”,期间我还写了一些关于当代作家的笔记。广东高教出版社黄红丽总编邀我编一本散文,于是有了 2022年出版、靳辉责编的《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这本散文的主体是“沧海文心”诸篇。许多事情都灰飞烟灭,但知识分子的沧海文心天地可鉴。我在这个专栏的写作中,找到了历史叙事的方式,也找到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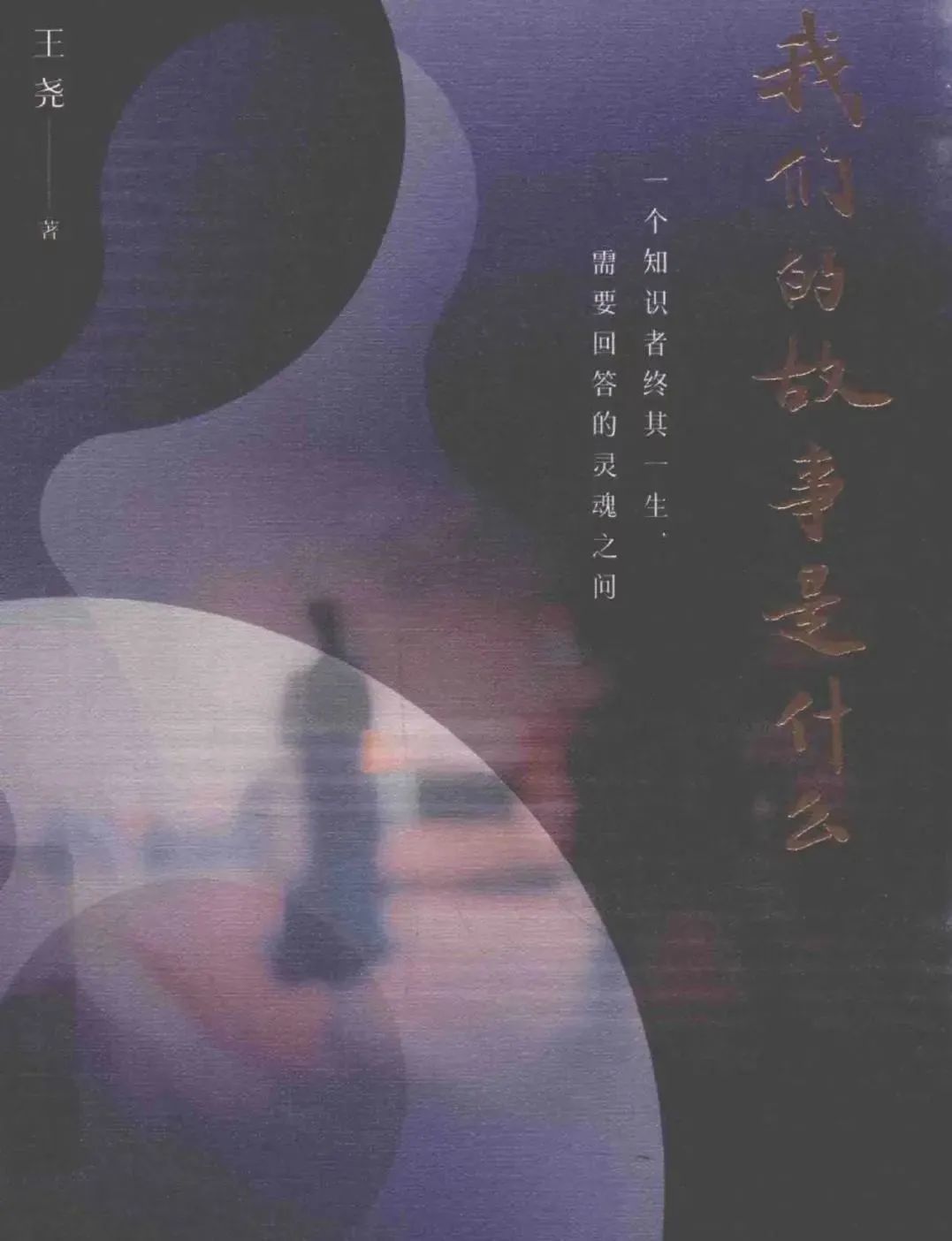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
《收获》专栏之后,我似乎一发不可收拾。《钟山》主编贾梦玮兄问我能不能再写一个专栏,我想起心中的西南联大,觉得可以写一组文章。和永新一样,梦玮兄也为我的拖稿头疼,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日常的弦歌》五篇文章。译林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民谣》时,规划了“王尧作品”系列,《日常的弦歌》纳入其中。我跟责编魏玮说,写了五篇意犹未尽,还想再写几篇。想写时,突然找不到感觉了,只好作罢。现在大家读到的《日常的弦歌》其实是一部未完成的书。这本书的跋传达了我的心境,我没有听过那些大先生们的课,但我是他们的私淑弟子。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西南联大的校门了。

《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
写作《日常的弦歌》时,《雨花》主编朱辉兄说了很多我应该给《雨花》写专栏的理由,我觉得很有道理,好像不好推却。给《雨花》写“时代与肖像”系列时,我已经进入了《民谣》写作的关键阶段,散文里的几个人物进入了小说,或者说小说中的几个人物也到散文里串门了。这组散文有热烈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李黎兄说,在我们社结集出版吧,这就有了2021年的《时代与肖像》散文集。李黎兄知道我喜欢用毛笔写字,特别提出要我自己题写篇名。写作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在写《雨花》专栏时,《上海文学》的来颖燕女士微信我,说应该给《上海文学》写专栏了。她特别提起很久之前就电话我约稿了,还说赵丽宏老师当面也邀请过我。我的重然诺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果然充分体现出来,说一定写,但我会拖稿。来女士说,不怕拖稿的。2021年《上海文学》上的专栏《纸上的生活》是我在艺术上最用心写作的散文,也是各种想象在语音中得以展开的文字。我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陈小真先生商量,出版时将书名改为《我是五月的孩子》。写作《纸上的生活》时,妈妈突然心梗离世,《拔根芦柴花》是我悼念妈妈的文字。妈妈五月分娩,我是五月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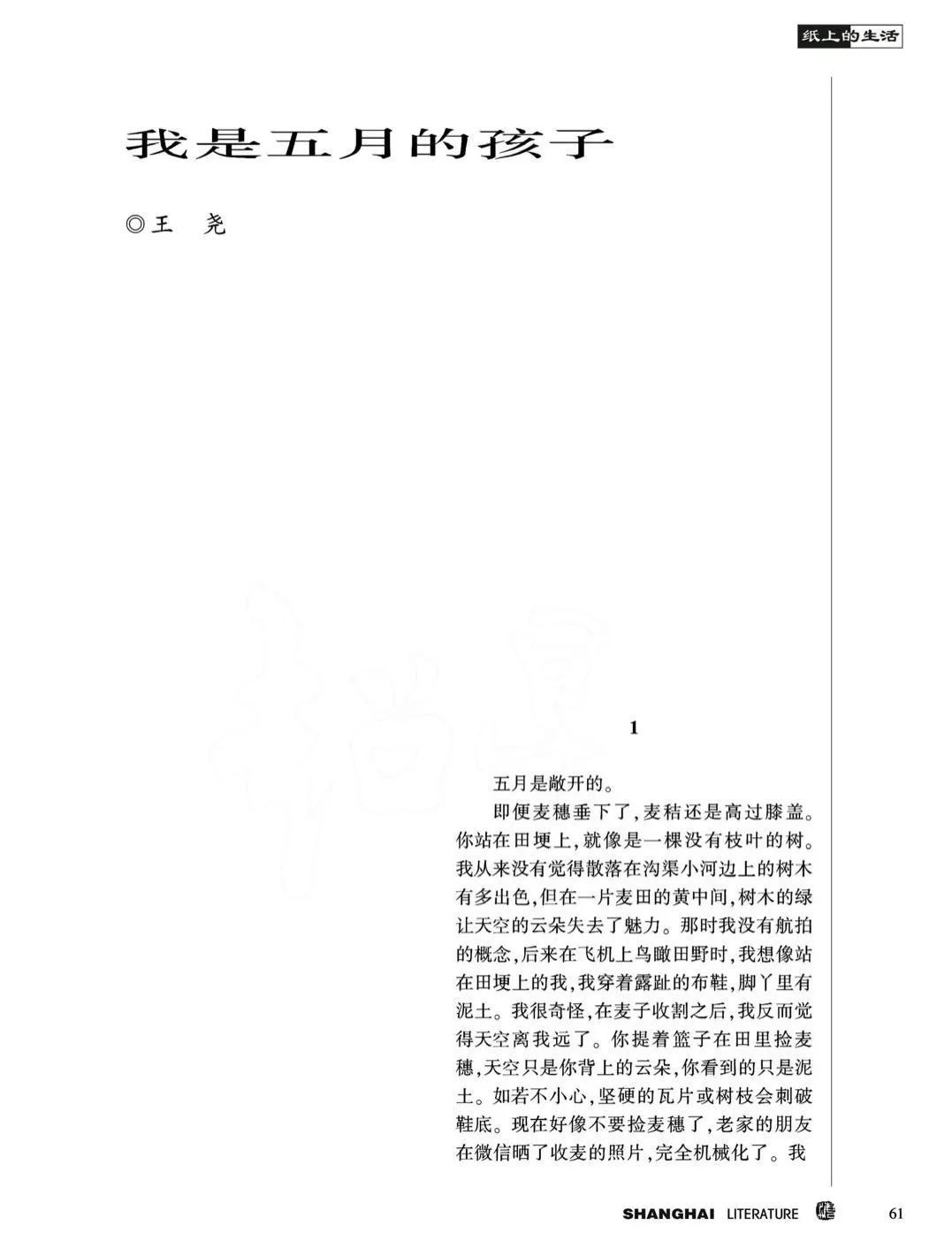
《我是五月的孩子》,《上海文学》2021年第7期
这么多年来,我好像陷在自己的陷阱中。我早期研究散文,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等。我一直在意中国的文章传统,鼓吹散文的非职业写作,提倡文学研究文体的文学性,等等。一个人一生都是在不停折腾,我是用文字折腾自己的那个人。许多时候,我也有虚无之感,所以我自警不要放大自己缩小世界,不必看重自己写下的种种。但有时又觉得,写作会让自己重返人生的起点,重新活一次。如果说,我的散文有整体性的话,那就是我给《脱去文化的外套》封面上写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长短录,纸上烟雨苍茫。
我研究了几十年散文,但我现在越来越说不清散文是什么。在许多关于散文的定义和艺术观之外,我希望自己的散文:有结构世界的能力,有和万物对话的能力,有再造汉语的能力,有文体交融的能力。我知道这只是梦想,是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的一部分,我乐此不疲。在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中,我写了这样一句开头:在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乐意识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河桥上张望的少年。现在的我,依然从散文的字里行间走过,偶尔伫立,问苍茫大地。我听到回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