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那个年轻时翻译过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写过一北一南两部地域文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山乡巨变》虽没有获得过任何奖,但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似乎比前者还要高,究其缘由,我想,除了文学本质的人性描写的艺术魅力外,就是对历史思考超越了当时一般作者对时代的盲从性,虽然许多批评家仍然感到不满足,但是,能够超越时代局限性的作家并不多,如今这样的叩问仍然会再次浮现,这就是作家如何“从历史链条看乡村世界”的书写逻辑。我们的作家是否具有观察这个历史巨变中的许多深层问题,用“第三只眼”去穿透“第四堵墙”,还乡村巨变中历史和当下的一个真实的面貌,其文学史的意义一定是指向未来的,其文学的“史诗性”就是让作品一直活着,让它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它在未来的阅读者当中,仍然保有鲜活的审美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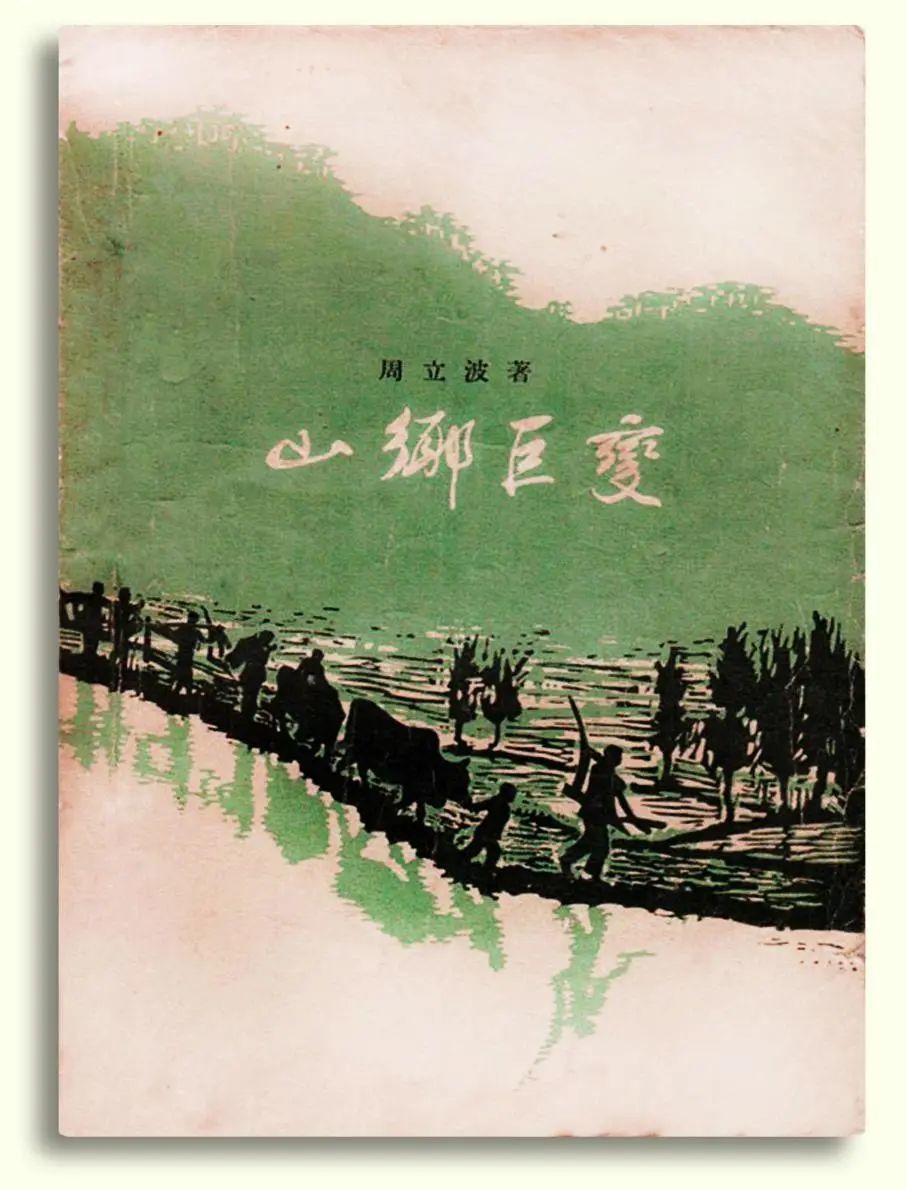
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为历史而战》一书中第四部分“文学史学家”中说,历史的逻辑“就要求作者本人就是读者。叙述者不入戏吗?他永远不说我吗?”这就是文学作品如何置身于外,从读者的层面来考虑历史和现实世界的耦合性;同时,他也需要置身于内,这就是叙述者要成为戏中人,用亲历者的“我”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之中,成为一个超越时空局限的独特的“我”,这样的叙述者才是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真实,还面向未来的作家,唯有此,其“史诗性”的作品历史逻辑才能实现艺术的回归。
当然,我并不同意作为历史学家的费弗尔批评文学史家时对“历史之历史”的文学史定义。但是,“要把它们写出来,就需要复原环境,就要想到该由谁来写,为谁写;谁来读,为什么读;……需要知道某某作家获得了怎样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如何;需要在作家的习惯、爱好、风格和成见的改变,与政治的变迁、宗教精神面貌的转变、社会生活的演变、艺术时尚和兴趣的改变等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见还是可取的。这不仅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参照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作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何将这种理念融入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方法中去,也是作家活在未来世界里的历史逻辑。
创造“史诗”并非只是唱诗和颂诗,也就是说,作家在回眸与歌颂农耕文明自然形态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在那种眷恋“麦浪滚滚”和“稻菽千重浪”的情怀背后,隐藏着多少农民的苦难和辛酸。如今当我们看到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农耕文明后,一栋栋华丽的别墅林立在湖畔沟渠旁,在歌颂工业文明给乡村农民带来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被污染的土地了吗?正因为我去年回到埋葬着我青春的故土中看到了另一种乡村巨变:河流被污染,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全是空巢老人,当我看见82岁的生产队长时,我的眼睛濡湿了……这一乡村风景与那些值得歌颂的工业乡村风景相比照,其文学的悲剧审美更能触动我的心灵,这种审美的落差正是作家审美价值判断的依据,反思这样的风景,我们才能让文学在现实的土壤中绽放出“史诗”的花朵。这是站在现实大地上向前看的作品,它无疑是构成“史诗”的重要元素。
那么,还有没有另一种构成“史诗”的重要审美元素呢?答案就在我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乡土小说自然风景画描写的消逝后的重新发掘之中。
由此,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兴起“自然文学”的书写,那是因为土地伦理价值观的崩塌,让作家对乡村描写进入盲区。当然,我并不同意“自然文学”以自然为中心的审美价值观,但是,现代工业文明将自然界的风景描写剔除在书写范畴之外,那就让“史诗”的书写缺少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对话语境。哈德逊河画派的艺术宗旨就是“以大自然为画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乡村小说的描写缺失就凸显出来了,作家已然没有了视觉之中的自然风景,故事与人物描写淹没了风景,殊不知,风景是构成乡村人与自然的重要纽带,对风景的盲视,就是对文学作品“史诗”元素的轻蔑。在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我选择的是两者平等的对位关系,这样才有利于作家在进入乡村描写时不至于在大自然景物描写中失明。无疑,在这次里下河水乡的文化考察中,站在高邮湖和宝应湖畔,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自然景观对于一个会思想的芦苇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多么希望作家能够在这样的画布中描写出风景中的人和人在风景中的像,“像山那样思考”才是作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融合,其中所漫溢出的人文意识和审美意识,才是作家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透视出的是一种永恒的人性,也是文学作品的艺术源泉。用这个画派的理论来说,“人并不因此而被淡化,反而与自然更强烈地融为一体,被壮丽的景观烘托得更突出。”因为他们相信,“人有生有死,文明有兴有衰,唯有大地永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文学胜于城市文学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忽略了这样的优势,是作家对审美的漠视。我们的国家,除西部还有着广袤的原野和雨林植被外,在中原和沿海地区,如果仅剩的乡村自然风景都被忽略了,我们就无法面对历史和未来的文学。
我并不认为在乡土文学中存在着“诗化”与“丑化”的两级标准,作家面对乡村的巨变,其价值理念首先是站在人性基础之上的,这是文学作品的首要条件。二十年前,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和骆玉明先生运用人性标准为经纬撰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让我醍醐灌顶。虽然有许多质疑的观点,但我觉得它是衡量世界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试金石,这才是文学最“本真”的力量。如果站在这样的视角上去反映一个大时代,你笔下的历史内涵和审美内涵就不会丢失,你笔下的所谓“新人”就不会走样,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就会如山泉一样自然流淌,浪漫主义的元素就会渗透在你的字里行间,变成一朵朵盛开的玫瑰。
今天,当我们与中国现代文学,也就是1919至1949年的文学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对《山乡巨变》这样作品的重新谱写,是否还容得下乡土文学开山之祖鲁迅式的那样充满着批判意识的作品存在?这的确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价值判断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当代乡土作家的书写沟壑。无疑,柳青模式和路遥模式的书写是被认可的乡村书写,但是,我们不能简单模仿他们的模式来处理当下乡村巨变的历史语境了。他们没能看到这几十年来乡村的巨变,我们总不能带着他们的历史局限性进入巨变乡村的描写之中吧,他们的价值观停止在“新时期”开端的钟摆上。由于工业文明,乃至于后工业文明给乡村带来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景观,如何面对巨变下的乡村书写,写什么?怎么写?是这个世纪文学给作家提出的历史诘问,没有一种恒定的价值观去统摄作品,作家哪怕就是依照人性的视角去构建自己笔下的故事、人物和风景,也会写出好作品,怕就怕你去套用一种流行时尚的模式去进行应景的写作,那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被拒之文学史门外的。
至于鲁迅风还适应不适应当下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正如恩格斯对文学作品下了那个普泛的标准观念那样,只要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就不能离开社会生活中的暗面,由于各个作家创作风格殊异,他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填写的价值观高度,选择价值观是他创作的自由,写光明和黑暗对于作家来说是同等重要的价值选择,任何力量都不应该挡住作家观察生活时的感受和经验。但是,面对“内卷化”的乡村,面对“低欲望的乡村生活”图景,作家当然不能闭上那双充满着良知的眼睛,我们不能站在一个城市艺术家的立场去奢侈地过原始人类的生活,也不能从日本“里山资本主义”那里汲取生活美学经验。在中国,对物质的追求和对城市的渴望,仍然是乡村农民的追求。即便是像梭罗那样离群索居的孤独者,最后也只能回到人类群居的文明中来。那么,只要活在人间,苦难就会自然而然产生,文学作品的高下往往是在于作家面对现实中的苦难采取什么样的审美态度,像雨果那样采取人性悲剧审美取向,同样可以流芳百世,人们会记住《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和《九三年》中充满着人性的悲剧,它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是一般作家作品不能比拟的,因为人性超越了时空,让他获得永恒。同样,鲁迅的乡土小说作品之所以还活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就是因为他作品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穿越了时空,照样行走在我们当下这个世界中。鲁迅不死,是指他笔下的人物还活在我们中间,所以一个世纪前的鲁迅乡土小说模式还适用否?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鲁迅不仅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思想家。
正好在网上看到李强的一篇题为《艺术一旦拒绝思想,就等于拒绝自己》的文章,其中说到:“艺术和宗教与哲学一样,是真理的负荷者,一旦艺术开始拒绝思想和真理,它就开始在拒绝自己了。……艺术作品的主题不能理解为素材,而应该理解为它所表达的思想,也就是它所蕴含的‘哲学’。”此言不虚,当为座右。
在乡村巨变面前,我们不能兼做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但至少我们应该学会做一个会思想的芦苇吧。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