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老屋,是在一个特有的绵绵秋雨中,站在当年的院门前,我无法移步,心里一遍遍问自己:这就是我魂系梦萦的家吗?是我和父母兄姐共同生活了18年之久的老屋吗?疑问被院里高高的两棵钉子槐树挡住。那是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亲自栽种的,它记录着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西院墙上斑驳的水泥粉底上依稀可见8个红色大字:“开门大吉,全家幸福”字虽小但有精神,活泼而不骄纵。那是30年前父亲年三十晚上回来教我在墙上写的,可今天它却浸透了生命原色,向我诉说无穷无尽的故事。
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院落,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院子里杂草丛生,砖砌半瓦盖,坐西朝东的厨房以及坐北朝南的三间正屋,门窗紧闭,屋顶上长满小草和许多嫩嫩的小树,虽小却还亭亭玉立。一只鸽子在树枝间探出疑惑的眼睛,不信任地看着我。我仰望属于院落箍紧的天空,云彩悠悠,让我开始感叹时光竟能开这样的玩笑:我还未老,童心依旧,我所经历的事情哪就这般老旧子吗?
房子是父亲过世的第二年卖掉的。
那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工资收入少,母亲只靠唯一的干部遗属补助维持度日,为了说上一门亲事,母亲决定将唯一的家底卖了。在决定卖房前,母亲在父亲的坟前转悠了三天三夜;在屋西的一块小地种菜种了三天三夜;用一桶桶水把幼菜嫩芽泡了三天三夜。在一个亲朋满堂红烛高烧的黄道吉日,母亲慎重地把用红娟包了十八道的订婚戒指和财礼钱交到我的手上,幸福的眼窝里泛动着心酸的泪水。
独自面对空旷,我的心变得湿淋淋,沉甸甸的。门板上有个洞,将眼凑上去,屋内杂乱堆着些物件,盯着屋角那些蜘蛛网,我的记忆粘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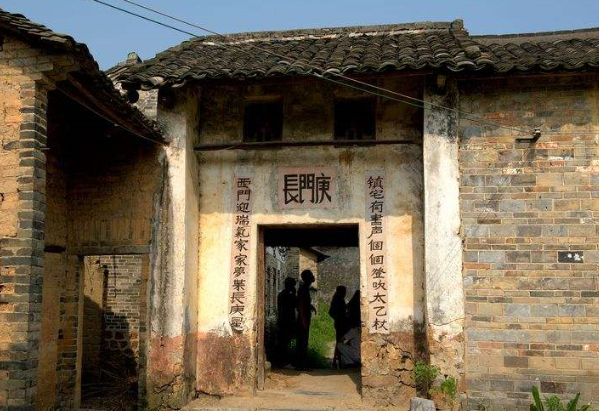

大哥,是我记事起最瞧得起我的人,他很欣赏我,教我唱儿歌,有时晚上皓月当空,他还带我到屋后小池塘边拉二胡、弹凤凰琴与我伴奏。大哥从城里学校毕业回来,由于父亲是“反革命”政治原因没有能上大学,就当上了教师,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小油灯一点就是半夜。他还买了很多药典、针灸医书,钻研医道。在我当时看来,他是我最值得尊重,天底下最有知识的人了。可是,是否应验了“好人不长寿”的话,大哥二十一岁就为自己的生命草草地划上了无奈的句号。
我记得那天下午太阳火辣辣地映在他的脸上,他无声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苍白,似乎没有痛苦,双手疲惫地垂在门框边,一双幽深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仿佛有很多话要说,一种苍凉通过这双明澈如洗的眼睛直逼我心。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拉住他的手轻轻地说:“大哥,我原谅你。”四周的人群都嚎啕起来,我不知道这间屋子里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只知道前天我丢了他的银针,他打了我两巴掌后步行二十里到小镇上买回银针,为邻村的一位老太太治病。他破天荒地打我,使我愤愤不平,童年开始的一切温馨、一切友谊消失殆尽,我决不原谅他,那天晚上我发过誓。然而眼前原谅与不原谅都已失去母体。大哥死了,他那身经过一番痛苦搏斗、泥迹斑斑的衣服都未脱去,甚至不知道为什么,那双依然睁着的眼睛,晶莹中含着永恒的眷恋。我没有哭,只是心中有一种刺痛在点点加剧,这是我懂事后第一次目击生命消亡过程。
大哥是我家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太倔强了,他的服毒自尽又是因为政治原因没让参军的缘故。以后我才明白生与死之间其实并没有鸿沟,生命与死神的抗争尽管惨烈,但它失败时并不仓惶。
大哥死后,母亲病得死去活来,总算活下来却整天神志恍惚,这种病一直延至到父亲过世。
逢年过节,为了防止她思念过度伤及多病的身体,我硬是将她接到我工作的单位。年三十晚上单位放假,我因值班不能和她一起回老家,就和她相对而坐在单位招待所的一间小房里,招待所四周的幼儿园、子弟学校都已人去楼空,原先热闹非凡的场景一下子静得彼此能听得见呼吸声。母亲示意我点上红烛,我就让母亲在烛光下听我拉二胡,她总是说:“你大哥拉的调子好听,他拉就像听了一本戏……”
正月初一,雪花纷纷,我陪母亲踏雪闹市,母亲说:“城里的雪花不比乡下的白,你爸被强迫传夜信的大雪天……”“妈,您快看那边腰鼓队……”我不想让她感怀,然而我的愿望没能止住她的眼泪。以后一年四季她下乡隔一条河看看那间老屋,冬天去了,雪花落满她的头发;春天到了,菜花簇拥她的视线。直到他意外地过世,我从她蓄满泪水的深深眼窝里看到的却只有我一个人。
不知什么时候,我走进院子,立在雨中,躲不过的回忆追逐着我,以一种浓如血色的氛围包裹我的灵魂。那是一个暮云四合的傍晚,风在小竹林萦绕,落日如烛辉煌而凄清。我和重病中的父亲来到这里照张相,亦可算作最后的留念吧。父亲站在一棵向日葵旁。他逗趣地说:“向太阳,死了也要向太阳。”向往光明对于一个活人来说可以说是本能,对于一个生命却将消亡的人来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生命的本身。我并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我想到家庭难以计数的坎坷,想到自身压抑而又充满抗争的心灵,我突然想哭,心里有一句话在回响:“愿英才崛起,参天大树屹立人间,我们的思想在深夜已经奋起。”我在喃喃低语,可父亲还是听清了这样的诗句,我们彼此注视着因天色昏暗而更明亮的眼睛,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父亲的去世,给了我双重打击,在我刚刚踏上人生舞台时,我突然失去了父爱、一位善于在逆境中前进的导师。同时我又因之失去了第一次恋爱。当我戴着白花在一条幽深的石板巷子里把整个小街踏得黑黑的时候,我手捂着遭受双重打击的心口问自己:我是那个黑人孩子吗?
或许这是青春勃发而又备感压抑的日子,它铸造了我百折不挠的探求欲和融于血肉的责任感。多年来我被这份责任感搞得疲惫而又无以解脱时,我不止—次地回想起那个黄昏,那个戴白花的黑天。我不得不面对青春的选择!这种回忆也不止一次提醒我,有种信念是铸进灵魂的,它无可变更!
我实在太傻了,在漫长的岁月,无论欢乐和苦痛,不是常常在灵魂深处与他们一次又一次进行彻夜难眠地交谈吗?我开始坚信他们活着,正如我时常排出他们的照片,他们依然对我微笑,往昔如水般地掠过全身,心中就有一种温爱的感动。每每这时,我对现实的险恶就又多了一份勇气,这种动力使我儿时就在学校挺身而出,演出无数场节日:小白鸽、愚蠢的大灰狼和聪明的小白兔……我不止一次地变换着行头,我仿佛一次一次地更新着自己。我不就是在中学时代提着那把大哥曾用过的二胡,在万人会场上演奏出《毛主席登上庐山顶》吗……当最后—只高音符找不到位置向空中飘去时,我却听到熟悉而整齐、响亮的掌声,直到我站到首都体育馆那辉煌的领奖台上,我还能从万人观众中看到他们为我挥手振臂!

站在空无一人的老屋前,我承认当年不止一次发誓要离开它,当我带走母亲时,我没有泪,也没回首,我以为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回来,这里一切离我远去,但青春无瑕,它属于我。我毕竟又回来了,却没有能把母亲带回来……
青山依旧,江湖常新,面对空无一人的房屋,我无歌无泪。不会唱当年那首合家欢了……然而我却明白人间一切却总不回头,又何必回头?有过痛苦、期冀、幻灭、抗争,生命在哪一点上停留,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为此,我又怎能不感谢生命给予我这一切呢?倒是包娜娜那首凉沉而感慨的《掌声响起来》实实在地填补了这份空白:“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易改,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掌声响起来,愿我心与你同在……”
■作者简介:曹峰峻 男 作家、记者、资深媒体人。 一九六四年生于江苏兴化,研究生学历,出版文学作品多部,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及新闻纪实作品近千万字;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八届公安文学奖”获得者;江苏广电总台文化期刊总编辑,现居南京。